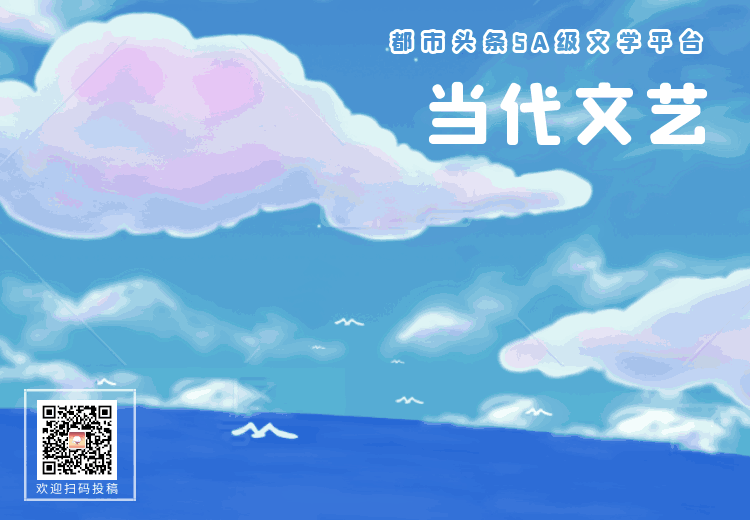苏军进驻小平岛二三事
文:乔世祯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西伯利亚方面军第三摩托化集团军在东北完成对日最后一战,歼灭关东军战役结束后,奉命挥师南下。他们日夜兼程,长驱直入开赴大连和旅顺,该军一个炮兵团则直接开拔到小平岛,驻扎在当地人称“小山”的地方。该团下属的一个炮兵连,在一名上尉连长的率领下,进驻岛南头一栋当地大汉奸逃走时丢弃的三层粉色小楼,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驻军生涯,于1955年10月撤军。
在这十年间,苏联红军与当地居民频繁往来,留下了一件件动人往事。尽管六十多年过去,那些情景依然像黑白电影般,不时浮现在当地百姓心中。下面撷取几个小故事,供大家分享。
当年苏军炮连在营区内经常放映电影,每当此时,连队领导都会安排士兵到驻地附近的老百姓家通知。那时候的岛上人,谁也不知电影为何物,第一次看到挂在墙上的大白布里出现声音、活动的人物和景物时,都不知所措地发出阵阵惊呼。几位老渔民甚至踱步到银幕前,试图用手去抓里面的人,引得正在看电影的苏军士兵不时发出善意的笑声。
炮连放电影的日子,是岛上大人小孩最快乐的时刻,堪比过年。大家都早早吃完饭,每人拎着个小板凳,结伴来到苏军营房,抢占最佳座位(当然不能占据炮连指定的区域),然后翘首以盼等待电影开演。那时岛上人沾了炮连的光,看了无数场电影。年轻人和孩子们最爱看反特片和战争片,有几部影片我至今记忆犹新,如《勇敢的人》《坚守要塞》《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深山虎影》《夏伯阳》等。尤其是影片里的夏伯阳,戴着哥萨克式高筒皮帽,留着胡子,挥舞着亮光闪闪的马刀,骑着骏马在草原上驰骋的英姿,至今令人难忘。
那时岛里人的生活十分窘迫,离市区又远,看不起病。家中有小孩患病,无钱医治,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夭折。之后凑几块木板,钉个小木匣子,把死去的孩子装进去,扛到南山或北山,挖个坑埋掉,有的甚至连坟头都不留。
家中老人曾对我说,我五岁那年,因感冒发烧、浑身出疹子,高烧一直不退。家里一时拿不出钱带我去市里治病,只能用土方,却丝毫不见效。眼看病情越来越重,已到了死亡边缘,父亲束手无策,母亲和奶奶只能以泪洗面——因为两年前,他们已经痛失一个五岁的女儿了。就在这走投无路之际,苏军炮团得知了消息,炮团首长立刻派一名女军医带着一名卫生兵,一路打听找到我家。进门后,女军医立即为我检查病情、打针喂药。经过两天的细心治疗,终于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全家人感动得一个劲地鞠躬致谢。
当年那位女军医约三十岁,肩扛一杠三花的军衔,身着白大褂,端庄文静,漂亮得就像苏联电影里的明星。在岛上的几年里,她治好了无数大人小孩的病,挽回了许多人的生命。直到她回国,大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当年,岛上的一些少年经常在苏军炮兵连旁边的火神庙大殿外空地上玩耍,那时玩的游戏主要是弹玻璃球、打小纸牌。每当这时,就有炮连的士兵三三两两围拢过来看热闹,看着看着,干脆蹲下身来,和我们这帮孩子一起玩打玻璃弹比赛。结果他们往往一个也打不着,气得直跺脚,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大概心里很纳闷:自己炮打得那么准,怎么一个小小的玻璃弹就打不着呢?
到了冬季,我们又常常聚集在炮连前一个叫“南泡子”的结冰湖面上,打呲溜滑、溜冰板、打陀螺,玩得不亦乐乎。这时,就会有十几个炮连的士兵溜溜达达地过来,先在旁边观看,后来实在憋不住,就先和我们玩打呲溜滑。由于他们穿着长筒皮靴,底厚皮硬、防滑性差,一摔就是一个跟头,只好败下阵来。接着又要比赛打陀螺,虽然他们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力气比小孩子大,但不会用巧劲,结果一鞭子下去,能把小陀螺抽上天。不服气的他们又要滑冰板,穿着棉军服的士兵笨拙地坐在冰板上,滑不出两步,就因没掌握好平衡,被冰板撅得摔个仰八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苏联士兵喜好摔跤,可在小平岛却遇到了硬茬子。当年我有个本家四叔叫乔传令,年方十六,血气方刚,一身力气,是全岛无敌的摔跤高手。这个消息被炮连知道后,便派人来约他比试。一天,一名排长带着几个连队里的摔跤高手,和四叔乔传令一起来到小平岛西海边的沙滩上过招。起初是一对一,不到两个回合,四叔就把那名士兵放倒在地。他们又上来两个人夹击,只见四叔一个扫堂腿把前面的人整趴下,接着一个弓背摔,把身后抱腰的大块头扔出丈八远,围观的人群纷纷拍巴掌喝彩叫好。那排长一看,嘿,这小伙子真了不起,便叫四个士兵一齐上——两个抱腿、一个搂后腰、一个正面迎战。四叔面不改色心不跳,沉着迎战,几个回合下来,把四个士兵全撂倒在地,在场的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那排长拍着四叔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嘴里喊着:“哈拉少,哈拉少!”几年后,四叔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空军战士。
一年夏天,几艘苏军舰艇驶进小平岛西口海域临时锚泊,岛上的人们都前往海边驻足观看这些从未见过的庞然大物。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心切,中午放学没回家,也顾不上吃饭,把书包堆在沙滩上,就下海径直向军舰游去,想一探究竟。从岸边到最近的锚泊军舰距离将近一千米,这在我们平时能游到的范围之内。游到离一艘军舰不到二十米远的地方,我们停下来仰头向舰上观望,甲板上站满了水兵,他们一边呼喊一边挥手,示意我们这些小孩子游过去登舰。游过去后,水兵们放下一根软梯,我们一个接一个抓着软梯爬了上去。
水兵们围着我们这些十岁左右的孩子,竖起大拇指,比划着夸赞我们勇敢,小小年纪就能游这么远。这时有两位老兵领着我们参观军舰的各个部位,我们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经过两位老水兵比比划划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是一艘猎潜舰,长六十多米。别看舰体不大,威力却不小,在二战期间的波罗的海一次海战中,曾击沉过德军一艘大型驱逐舰,真是了不起!我们对这艘战功卓著的战舰肃然起敬。两位老兵又带领我们观看了舰尾的鱼雷发射装置,随后领到舰首的主炮位置——那是一门双管炮。按照他们教的操作要领,我们每个人都上去摆弄了一番,手握操纵柄让炮管上下左右飞速旋转,乐得大家嘎嘎大笑。这时一名水兵拿来一架望远镜让我们观景,远处的山峦一下子就“跳”到了眼前,清晰得惊人,我们差点把望远镜掉到甲板上,逗得水兵们哈哈大笑。
时间过得真快,几个钟头转眼过去。由于中午没吃饭,我们一个个饥肠辘辘。得知我们还没进食,两位老兵领着我们走进舰上的饭厅。这个饭厅不算大,估计能容纳四十几人就餐,却布置得十分温馨。正当我们东张西望时,两名水兵端着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放着白列巴、奶油、香肠、水果等食物,他们把食物放在餐桌上,又拎来几瓶饮料,两位老兵示意我们用餐。我们从出生以来,整天吃的不是苞面饼子、苞面糊糊,就是咸鱼、咸菜、萝卜干,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精美的食品,也顾不上客气,风卷残云般大嚼起来,一个个连吃带喝,撑得直打饱嗝。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时候不早了,我们怕家里人担心,便提出要回去。舰上的水兵也催我们早点回家。来到甲板上,我们和水兵们一一告别,他们逐一拥抱我们,依依不舍。之后我们从甲板上“扑通扑通”跳入水中,钻出水面后,又向舰上的水兵们挥手,他们也朝我们挥手,嘴里还喊着什么,大概是叫我们注意安全吧。
正巧这时有几只在海上钓鱼的渔船归来,邻家的大叔们把正在水中游动的我们接到了舢板上。坐在船舱里,望着渐渐远去的军舰,我们的眼睛模糊了。亲爱的水兵大哥们,以后或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你们的友情,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中。
那年一个秋日的星期天上午,苏军炮兵连营区里走出两名士兵,每人手里提着一个草绿色帆布水桶(专门给马饮水用的),径直来到一户平时交往不错的当地老乡家,借了两挂钓鱼线,然后顺着门前小路向南山方向爬去。走到半山坡时,两人各折了一根棉槐枝,撸去树叶当作钓鱼竿。他们登上山顶一个叫“小楼”的地方停下——这座小楼是苏军之前废弃的观通站。这里的山顶距崖底有五十多米高,山崖陡峭,十分险峻。两名士兵站在山顶四处观察崖底的线路,随后开始顺着崖面小心翼翼地攀岩而下。由于手里提着帆布水桶,又拿着钓鱼竿,再加上脚上穿着长筒军靴,行动十分不便。他们一点一点往下挪,当爬到离崖底还有七八米高的地方时,一名士兵一脚踩空摔了下去,另一名士兵没拽住他,也跟着掉了下来,两人重重摔在崖底的礁石上,身下流出的鲜血染红了眼前的礁石。
正巧有几只在附近海面钓鱼的渔船,船上的人发现出事後,立即收起渔线,飞快地摇着小船靠近礁石,几个人把两名士兵抬到船上,迅速向小平岛西口摇去。靠岸后,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这两个因失血过多已奄奄一息的士兵,抬到两百多米远的炮连。卫生兵进行一番紧急处置后,又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四五里地外的苏军疗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由于救治及时,两名士兵的伤情转危为安。
后来有一天,连队领导带着这两名士兵,提着礼品来到参与抢救的渔民家中答谢。而我们的渔民却说道:“我们更应该感谢你们,你们为我们当地人看病疗伤,救了那么多人的命!”
寒海冬游
寒冬腊月的一天,乌云蔽日,北风呼啸,天空中飘着的小青雪还没来得及落地,就被西北风刮得无影无踪。我闲得无事,站在外屋窗台上,向不远处的西口海面望去,只见被西北风掀起的浪花涌向南山崖底的礁石,摔得粉碎,涛声轰鸣。正当我看得入神时,耳边传来阵阵苏联歌声。不一会儿,从炮兵连方向走来一队排着整齐队列的士兵,大约一个排的规模,径直来到沙滩上,随后排成三列横队。只见一名“戈比蛋”(苏军军官的别名)走到队前喊口令,无非是稍息、立正、向右看齐、报数之类,接着训话。最后一声口令下达,士兵们纷纷摘帽脱靴、脱下大衣,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们竟脱得一丝不挂,白晃晃的刺眼。只听他们齐声呐喊着,一窝蜂似的向海边冲去,纵身跳入水中。
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时只见水性好的士兵以优美的自由泳姿游出近百米,水性稍差的则在沙滩边的浅水里,用“狗刨”式扑腾着。大约二十多分钟后,站在岸上的军官一声令下,士兵们聚集到海边齐腰深的水中,开始玩“骑马打仗”的游戏——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分成两帮交战,把对方打倒在水中就算获胜。我在窗里看得真切,这不是我们小孩经常在海里玩的游戏吗?他们怎么也会,莫非是偷学我们的?
又过了一会儿,军官再次喊话,水中正打得不可开交的士兵们立刻跑上岸边放衣服的地方,拿出毛巾擦拭冻得通红的身体,然后迅速穿戴整齐,站好队形。随着军官的口令,士兵们向右转、齐步走。这会儿他们没有唱歌,大概是冻得唱不出调了,而是喊着整齐的队列口令:“得爪是利”,大概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听着渐渐远去的口令声,我仍在回味着苏军士兵在冰冷海水中冬游戏耍的情景,心想:这真是锻炼意志啊,这些来自北方的士兵可真抗冻!
士兵与年夜饭
我家前街有个刘姓大叔,四十多岁,以倒卖鱼货为生。他经常到炮兵连营房卖鱼,一来二去,和这里的一些士兵混得很熟,尤其和几个老兵更是亲如铁哥们。这年大年三十,他决定请这几个士兵到家中吃顿年夜饭,让他们体验一下中国年的味道。为了备好这顿饭,他趁着年前去市内贩鱼的机会,购置了鸡、鸭(鱼家里本来就有)和猪肉,还特意多买了些牛肉——因为苏联人对牛肉情有独钟。此外,他还买了几瓶二锅头、啤酒等,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岛上有个风俗: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大人小孩都要提着小灯笼到北山一带的自家墓地“请神”(就是把先人请回家过年的意思)。因为要请客,刘大叔在大年三十下午,太阳还没落山时,就独自一人拿着烧纸和几炷香,匆匆来到北山自家坟地。他把香点上插好,烧了几刀烧纸,磕了几个头,嘴里嘟嘟囔囔说了几句,算是把老祖宗请回了家,然后急急忙忙往家赶。到家后,他在了你外屋的供桌上摆好祭品、点燃香火,便和家人一起忙活晚上的大餐。刘大叔的厨艺不错,他常年在市内卖鱼,经常下馆子品尝各种名家大菜,也能做出几道像样的佳肴。不一会儿,各种菜肴的香气就弥漫了整个小院落。
晚上六点整,炮连的五位老兵准时赴约,个个穿戴整齐。没想到他们还挺懂中国人的礼数,入乡随俗每人都带来了礼品:有的拿着黑列巴,有的提着奶油、香肠,有的带着雪鱼罐头,还有一个士兵带来了一件新发的内上衣。这可把刘大叔一家乐得合不拢嘴,一边接过东西,一边热情地往屋里让。士兵们进屋后,看到供桌上摆放着老祖宗的宗谱,赶忙立正站好,给老祖宗敬了个军礼,还不忘上前炷香。这时,里屋的饭桌上已摆满了丰盛的酒菜。刘大叔请他们脱衣摘帽、褪去皮靴上炕,由于他们不会盘腿而坐,便每人给了一个小板凳。
刘大叔给每个人的酒杯都斟满酒,然后端起自己的酒杯致开场白。他用半生不熟的俄语说道:“感谢你们来家中做客,中苏两国人民都是好朋友!”说完,他先干为敬,一口喝干了杯中白酒,又倒满一杯,和大家一同饮下。随后,他招呼大家吃菜。苏联士兵哪里见过这么丰盛的佳肴,立刻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们不会用中国筷子,笨手笨脚地把菜扒拉得到处都是,引得家人哈哈大笑。刘大叔赶紧让女儿把早已准备好的刀叉拿过来,每人一套。这下他们可得心应手了,熟练地用刀叉进食,大口咀嚼着,一边吃一边不停地喊着“哈拉少,哈拉少”,一个劲地称赞:“中国菜太好吃了!”
酒过三巡,三瓶六十度的二锅头已经见了底,大家都喝得酒酣耳热。这时,外面街上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天色不早了,几位士兵也有些醉意。他们怕耽误回军营的时间,便起身穿好衣服,踉跄地走到外屋,和主人寒暄告别。就在这时,有两名士兵趁主人不注意,把供桌上的祭品全都划拉到了大衣兜里。等全家人送完客人回到屋里,才发现供桌上已经空空如也。刘大叔苦笑着说:“这些‘骚挞子’(苏军士兵的别称)可真能折腾!”没办法,他只好又拿出一些瓜果梨枣、点心之类的东西重新摆上。
195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天空蔚蓝,艳阳高照。这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与苏军将举行交接仪式,苏军即将撤离小平岛。我们都早早地来到现场观看。只见一支穿着崭新草绿色军装、肩扛各种轻重武器的队伍,唱着嘹亮的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由小平岛北面向岛南头挺进——他们是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边防团的一个连队,奉命前来接管苏军炮兵连的营地并完成交接任务。
此时,街道两旁已挤满了当地居民,大家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争相目睹这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人民子弟兵的风采。行进中的解放军官兵也纷纷挥手,向老乡们致意。
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姓邵的老汉。十多年前,他唯一的儿子离开家乡,只身前往北方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从此杳无音讯。直到两年前,市人民政府送来烈士证书和立功奖章,他才知道,身为志愿军连长的儿子已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今天,这位老人看着这些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与此同时,苏军炮兵连的官兵也穿着新军装,整齐列队在营区前的空地上,等待解放军的到来。训练场上排列着十几辆军车和十几门火炮,擦拭得锃明瓦亮的炮身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随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声,我方边防连官兵威武地来到场地,与苏军炮兵连官兵面对面列队。交接仪式正式开始,双方各走出一名军官,相互敬礼、握手致意。我方军官首先说道:“从今天开始,你们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随后,苏军军官致词:“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把营区完整地移交给你们,望你们尽到保卫祖国的使命。”
接下来是升降国旗仪式。首先,苏联那面镰刀锤子旗缓缓降下;紧接着,两名解放军升旗手双手捧着五星红旗,正步走向旗杆下,将我们的国旗徐徐升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旗杆顶端迎风飘扬时,现场的战士和群众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几位年逾古稀的老渔民看到眼前的情景,感慨万分、思绪万千。他们曾经历过日本统治下四十年毫无尊严的亡国奴生活,后来苏军光复大连、进驻小平岛,人们的生活状况才慢慢得到改善。但那毕竟是别国的军队,如今,我们国家自己的军队进驻,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扬眉吐气。
交接仪式结束后,两国士兵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有人情不自禁地把军帽抛向空中。只听到苏军士兵高喊着“乌拉”,我方战士则高呼“万岁”。
上午十一时整,苏军士兵列队登上十几辆牵引着火炮的军车,在汽车引擎的隆隆声中,依次向北驶去。这时,街道两旁的人们在欢迎了解放军队伍后,又变成了欢送苏军的队伍。大家挥舞着中苏两国的小国旗,高呼着“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口号,与苏军士兵作最后的告别。车上的苏军士兵看到车下熟悉的老乡,拼命挥手致意,并敬上最后一个军礼。
这时,我和小伙伴们发现其中一辆军车上,有两个我们平时最要好的士兵——一个叫瓦西里,个子不高,长着娃娃脸,脸上还有几粒雀斑;另一个叫阿廖沙,个子稍高,长得比较壮实。他们都是十八九岁,是去年初从苏联国内调来轮换的士兵。
我小时候因为感冒影响了鼻子,说话有时会囔囔的。这两个士兵就学着我的腔调说话,气得我直骂他们,可他们不但不恼,还哈哈大笑,故意逗我。不打不成交,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铁哥们,闲暇时经常和我们这帮半大小子一起玩耍,有时还会到我们家中串门。相处的时间久了,我们跟着他们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苏联话,他们也跟着我们学会了几个汉语单词。有一次,瓦西里从怀里掏出一张全家福照片,指着其中一个穿军装的帅小伙,比比划划地告诉我们,那是他的大哥,一名坦克兵,在二战后期攻打柏林的战役中壮烈牺牲。阿廖沙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叔叔,也在二战的战场上为国捐躯。看来,德、日两国法西斯是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共同敌人。
这时,车上的瓦西里和阿廖沙似乎也看到了我们,用力地向我们挥手呼喊,还不时用手背擦拭眼睛。我们也不停地向他们挥手,高喊着他俩的名字,追着车子跑了好长一段路。望着渐渐远去的车辆和消失的人影,心中涌上难掩的不舍之情,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再见了,亲爱的苏军老大哥!再见了,亲爱的朋友!祝你们一路平安,早日回到遥远的祖国和久别的家乡!
【作者简介】
乔世祯,生于1945年,1962年参加工作,大连水产养殖集团工作一直于2002年退休。退休前多年担任集团下属书记工作,1984年在职就读大连工人大学中文专业,1987年毕业。本人爱好写作,参加工作第一年18岁时就写出第一篇文章《我的船长》如今我已80余岁,仍钟爱写作。愿在书田耕耘中,寻找人生快乐。现为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2024年荣获中共中央颁发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当代文艺总社机构设置
一、总社社委会
1. 荣誉社长:李清华 王根杰
2. 社长:陈顺灿
3. 总编:武墨菲
4. 副社长:雷学业 李葆春 李晓云 杨山坡
5. 秘书长:周艳芳 副秘书长:张鑫
二、分社社委会
1. 大连分社
社长:李葆春 副社长:刘兵 宋连生
2. 湖南分社
社长:雷学业 副社长:吕晓蓉 段文华
3. 安徽分社
社长:蒋四清 副社长:张北传
4. 湖北分社
社长:张良碧 副社长:张鑫
三、顾问委员会
顾问:欧阳戈 石会文 鲍厚成 高秀群 王玉权 张泽新 张铭玉 陈晨 周葵 王瑞初
四、编辑委员会
主编:武墨菲(兼)
副主编:李晓云(兼) 郑暹琼
编委:李文杰 彭葆平 段文华 张良碧 张鑫 吕晓蓉 蒋四清 卞玉兰 郝文鹏 张北传 梁小芳 彭厚锋 黄勇彪 王红霞 邱光军 李春莲 周艳芳 乔世苓 王正元 刘廷荣
五、编辑部
1. 主任、责任编辑:武墨菲(兼)
2. 助理编辑:(空缺)
3. 总社诗会期刊、专刊收审稿专员:由编委会成员兼任
4. 作品政治导向审核把关:陈顺灿 雷学业 张北传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