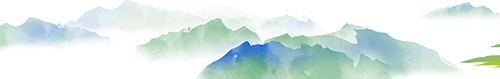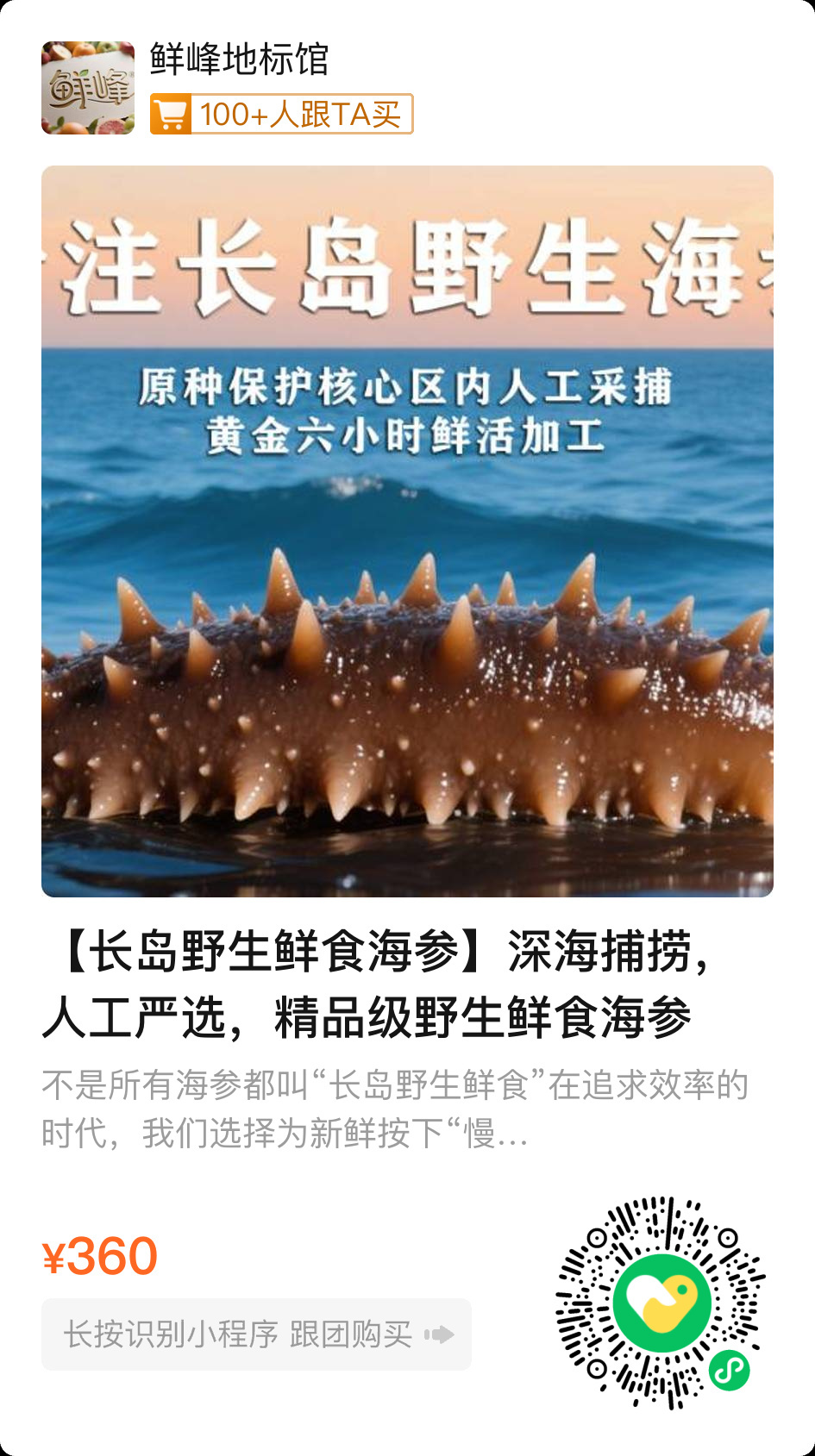一个识文解字的傻子
——“愣大仁”
亦 金

我在济南出版社出版的《白旄楼》的散文集中,在《娘的口头语》一篇中,写到了我们村里一个识文解字的傻子“愣大仁”,所写内容只是局限于我娘与村里一些好心人关照“愣大仁”的一些事情。有不少读者,希望我提供“愣大仁”更多鲜为人知的情况。
“愣大仁”,本名叫刘居仁。“愣大仁”则是后来村里人们送他的外号。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们把傻子,称为愣子。因为刘居仁傻,又在兄弟俩中排行老大,也就叫他“愣大仁”。“愣大仁”挺出名,不仅在我们村子,就是在周边庄里,几乎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
在村里,那些曾经有头有脸的人物,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钱多的,死去没有多少年,人们也就淡忘了,很少再去提及,似过眼的烟云。而“楞大仁”却不一样,虽然已经死去几十年,但人们还还在念叨他,大概因为他是一个太过特殊的悲剧性人物,也就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一直让人们回味着。
“愣大仁”生于一个财主家庭。一直到他父亲那辈,在我们村里还是数一数二的丰衣足食的大户人家。他在家塾中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村里是最系统的读过程朱理学的人,也是认识繁体汉字最多的人。村里的老人都说:“别看愣大仁傻,可装着一肚子学问,他没有不认识的字,啥字也难不倒他。”
对于他的变傻,村里村外的人众说纷纭。
“愣大仁”大概是1920年前后的生人。论年庚,与我父亲差不多,但要比我父亲小几岁。早年,我父亲常在他家里当雇工,对“愣大仁”甚为了解。我曾问过父亲“愣大仁”是啥时候才变傻的。父亲告诉我说:“他从小就看着不大精明,与正常人不大一样,谁知年龄越长,书念得越多也就越傻了。”父亲给我讲了一个他年少就不大精明的例子。在冬季里,父亲往他家地里运送肥料,以备春耕。在肥料堆放地点上,他与父亲发生争执,差点打起来。父亲要把肥料堆放在田中最高处,说是防止被雨水冲走,而“愣大仁”却要把肥料堆放在田中最低洼处,说是放在低洼里雨水就冲不走了。“愣大仁”回家,在他爷爷面前说父亲不是,他爷爷一听火了,踢了他一脚,说是少心眼少的吃地瓜都不知道倒把了。父亲还告诉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县上曾有人来找过他,想用用他的学问,一接触,发现他确实有些傻,也就黄了。对他的傻因,村里人和外村人,比较流行一种说法,说“愣大仁”太痴迷于读《易经》,读得走火入魔了,才变傻的。更有甚者,传说他不是一般的精通《易经》,会使用法术,拘神拘鬼的。
在中年时,傻到不能自食其力的“愣大仁”,才在家庭破破碎的困厄中,沦为以乞讨为生的流浪汉。初来,他虽然傻,但还有爹、娘和妻子照料他,在他的爹、娘先后死了以后,他的妻子立时变了心,翻了脸,把他像一块破抹布一样抛弃了,带着家里的财物,也带着他的儿子,改嫁另人了。他妻子嫁给的是村中本族的也是一个地主成分的叫刘居五的人。村里知道内情的人说:“刘居五是趁火打劫,把愣大仁的妻子儿子抢走了。”在这种情形下,“愣大仁”也只有流浪乞讨一条路可走了。
在我离开故乡时,“愣大仁”已经五十多岁。每次见到步履在大街大巷的“愣大仁”那种罕有的悲怆模样,就特别扎心。“愣大仁”的神情一直是木木呆呆的。他几乎不说话,也没见他笑过、怒过、哭过……就是一个木头人儿。他那双眼晴,虚设的一样,不会用来看这儿、瞧那儿,就连身边经过的人,也不会转动一下眼球望一望,只是默默地低头看自已脚前延伸着的道儿。“愣大仁”近乎是嬷嬷嘴,下巴上仅有的几根胡子,也不见怎么长,但脑袋上的头发却疯长。在头几年里,他一年或几年都不理发,那太长的头发堆在头上,像个乱蓬蓬的柴火垛子,后来,村里理发店的老孙头,实在看不下去,会给他一年里理上个一次两次的。“愣大仁”穿着是“捆绑式”的。也不知那个好心人,在冬季送他一件破棉袄和一条破棉裤,这仍不足以抵御特别寒冷的天气。他就不断往身上添加物件,把讨来或捡来的破旧的棉布块、麻袋片、棉花套子、塑料布等,缠绕在腰上、胳膊上、大腿上,再用草绳子一圈一圈地捆扎起来,就像斑马纹一样。从来没见过他穿过正儿八经的鞋子,他用捡来的破布条条,把两只脚一层加一层的缠裹起来。夏日,缠裹的薄一些;冬日,就缠裹的厚一些。那两只缠裹的脚,有时像两只小船儿,有时像两个喜鹊巢儿,有时像一对大流星锤儿。村里的一个老高中生,编了一个调侃“愣大仁”的顺口溜儿,说他有“四大怪”:“一脸好无奈,头发似伞盖,身子缠绳条,裸体沙滩晒。”这后一句“裸体沙滩晒”,是说“愣大仁”有一个自我健身的秘诀,在天气最热之际,跑到小沙河里,在流水中浸泡一阵子,便躺在热沙子上翻来覆去烙上一阵子,一烙一个月,直烙的“黑炭头”一样。他持之以恒,年年都这个样子。村里的人,对“愣大仁”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外村的人,特别是一些文化人,则把“愣大仁”看成是一个非常神秘人物。有的说他像欧州人的,有的说他像太空人的,还有的说他像苦行僧的。
说他流浪汉,他也是只在本村里转悠,从来没有去过别的村子。也许他觉得在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上才是最安全的。村里人说:“这愣大仁属小家雀的,就认准一个屋山头了。”“愣大仁”大多在每天早与晚两次上门讨饭,只是立在人家大门口,靠在门框上,也不吱声,连个三叔二大爷也不叫,在那里默默等待一会儿,人们没发现他,或者发现了不给他,也就转身走了。时间久了,他也就摸清了谁家会给与不给,以后就专上给饭的门,去定点讨饭。在村西头,他去的最多的是大队书记家,每次都会给他要饭的瓢里盛一碗稀饭,有时还会给他一个煎饼。在我们三弯巷里,他去的最多是我们家和二叔家。我娘见他来了,就叫我们给他讨饭瓢里多盛两勺稀饭,还要加上一块地瓜。我娘说:“太可怜,多给点,叫他少跑几个门。”“愣大仁”有时太过饥饿,会饥不择食,跑到人家菜园子里拔萝卜、薅韭菜吃,人家物主发现了,也不会打他骂他,或训斥他,说是一个傻子知道什么,要不太饿,还会吃这个。有一次,“愣大仁”又去人家菜园子薅韭菜吃,他不知道“葱辣嘴,蒜辣心,韭菜辣断脖子筋”,吃的太多了,直辣的昏死过去。人家物主发现了,赶紧把他拖到大树荫凉下,又从井里打来清凉水给他灌下去,才使他慢慢苏醒过来。
“愣大仁”居无定所,一年四季里,大多落脚在村中的一间被人废弃的破屋子里,那破屋子无顶、无门,也无窗,只剩下一圈土坯墙的框子。村里有些缺少教养的孩子,常在黑夜里,向屋框子里投掷石头瓦块,以砸中“愣大仁”取乐儿。这时候蹲在墙角的“愣大仁”,会把要饭的瓢扣在头上,像个鸭嘴兽一样,以防石头瓦块击中头部。向里边抛掷再多的石头瓦块,他也不会走出来,也不会骂人,只是不停地喊着:“俺娘啊,俺娘啊……”有时在大白天,也有些缺少教养的孩子,跟在“愣大仁”身后边,向他身上投掷石头瓦块,被打破头和脸的“愣大仁”,只是用手擦一下血迹,连眼皮也不抬,一声不吭的慢吞吞地走了。大队干部知道了这些事情,非常生气,在全村社员大会上讲:“愣大仁,也是人,也是一条命,有的人家的孩子(点了几个坏孩子的名),是怎么教育的,用石头瓦块袭击他,这是犯法,砸死了,能白砸死,也得去抵命。”我家东邻叫站迎的孩子,就在晚上捉迷藏的时候,好几次向破屋子里投掷石块瓦片去砸“愣大仁”,他爹开会回来,一进门就把这孩子按倒在地,脱下鞋子,朝他屁腚上一顿猛打,打得像被杀的猪一样哇哇叫唤。自从大队里出面阻止这种行为,这种事儿就渐渐少了。
这“愣大仁”的确有别于其它傻子,他有一个最大的癖好,就是在村里大街小巷的墙壁上,包括屋墙上、院墙上和厕所墙上,不停顿地写字,无休止地写字。他整日写啊写啊,似乎还沉浸在往日对典籍的兴致里。写字使用的是由他自已捏合成的石灰粉团,还有取自废弃电池的石墨棒。他所写的内容,是几乎没有人完全看懂的“四书”“五经”的章句。村子里所有能写字的墙壁上,都被他写的字覆盖了。前边写上的字,若被雨水冲刷掉了,他就会再去重新写上。我家前边的一排房子,为青砖垒砌,“愣大仁”最乐意在那里写字。我那时才上小学四年级,虽然对他写得繁体的之乎者也的内容看不大明白,但出于好奇,常躲在他背后看他写字。他三个指头,捏住一个苹果大小的石灰粉团,不停地转换角度,写得飞快,每一个字,都笔划均匀,十分工整,比我们老师的板书漂亮多了。有一次,我看到他写下的一个不认识的“淼”字,就问他:“大仁,这三个水的字念什么?”他悄声回答:“淼(mⅰǎo)”。我又问他:“讲什么意思?”他又悄声回答:“大水,齐头水。”我真得难以琢磨,这些章句,还有读写,都是在他还不太傻的时候学到的,怎么变得这么傻了以后,还能够记得这么清楚和牢固呢。看来,他对曾经学过的书本知识,已经刻在骨子里了。“愣大仁”虽是地主的儿子,但由于是个傻子,村里从来设有把他列入“管治”之内。他是“自由”了,却给村里大队干部带来不少麻烦,每当村里进驻这工作队那工作组的,都要把“愣大仁”当政治问题,过一遍审查的筛子。尤其是“四清“运动那年,进村的“四清”工作队中,有两个北京的大学生,初来接触“愣大仁”,感到很神秘,很怪异,以为发现了大问题,在暗中观察研究了他好些日子。他们向大队干部提疑问三条:一条是“愣大仁”是不是故意装傻,以逃避管治;一条是“愣大仁”是不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挖出来;还有一条是这些看不大懂的内容,是不是在搞反动宣传。大队干部听了觉得太搞笑了,但怎么去解释人家也听不进去。大队书记急眼了,拍着胸脯子说:“愣大仁要不是傻子,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开除我的党籍,让我坐牢去!”那两个工作队的大学生,听了大队书记掷地有声的表态,再加上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据我观察,“愣大仁”虽说傻,但也有清醒的时候,也是有一定认知能力的。至于他有着怎样一个内心世界,还藏着怎样的秘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我曾多次听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刘居五,刘居五,抢妻夺子,罪该万死……”从中可以看出来,他对占有他妻子和儿子的刘居五是耿耿于怀的,十分怨恨的。“愣大仁”常去一个叫刘建仁的家里讨饭,看到他家房内墙上挂的大玻璃框子里,装满了黑白与彩色的照片,他对这个新发现,也曾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刘建仁家,有一千张照片。”我知道,刘建仁家的照片有个百儿八十张的,但也没有上千张,他这是用上夸张手法了。“愣大仁”将自已的认知写在墙上,我仅过见两条:一条是他看到人家堆放在大街上的苘麻果实,就从果壳里扒出种子来吃,他可能认为味道不错,丟弃可惜,便在墙壁上写道:“苘种是好粮食”。另一条,则与我有关系。那时候,我是农民通讯员,爱写个广播稿,也会把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张贴在宣传栏里。与我一块儿搞通讯报道的刘步溪,告诉我说“愣大仁”把你写墙上去了。我跟他过去一瞧,果真在墙上写着:“x(我的乳名),刀笔”。我至今也弄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我的乳名和写过稿子的。
“愣大仁”在村里,并非举目无亲。虽说他妻子另嫁别人,但跟随妻子离去的儿子,己经成年。在村里广为流传一个称谓,即“居吉、小黑、愣大仁”。所表达的意思,既是说这三个人有最亲近的关系,也是说他们三个人是“差得不能再差、孬得不能再孬”的人物。这居吉,叫刘居吉,为“愣大仁”的亲弟。这小黑(乳名)是刘居吉儿子,也是“愣大仁”的亲侄。这刘居吉早早死了妻子,与儿子小黑一起度日。这小黑是村里三个有哮喘病的人中最为严重的一个,不能干重体力活儿,生产队安排他去掏厕所大粪。村里人有目共睹,“愣大仁”的这些亲人,还不如其他乡亲们,对“愣大仁”没有任何关照过。过年的时候,村里有不少乡亲们,都会去送给“愣大仁”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说是:“咱过年了,也不能让愣大仁吃不上饺子。”但“愣大仁”的那些亲人们,却没有一个去送饺子的。尤其小黑,还在外边对“愣大仁”咒死咒活,说是:“这个熊玩意儿,还不如早早死了。”村里人都说小黑是顶着张人皮下了生,没个人味儿。在腊月里最寒冷的日子里,尤其是碰上下大雪的天气,“愣大仁”会钻入一些人家的地瓜窖子里,在里边既能暖和些,也能饿了生食地瓜。对“愣大仁”的这种行为,人们可怜他,十分容忍,从来没有人伤害过他。在一年腊月里,那是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愣大仁”钻入了他侄子小黑的地瓜窖里,才住了一个晚上,就被小黑发现了,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抄起一把铁锨,对着“愣大仁”狠劲的铲了下去,那铁锨铲在了“愣大仁”的左脚上,把五个脚指头齐刷刷地铲掉了,“愣大仁”疼痛地昏死过去。居住在小黑家附近的几个老人知道了,把小黑围起来痛打了一顿,又把村里的赤脚医生找来,把“愣大仁”被铲伤的脚用药包包扎了起来。在这之前,“愣大仁”的儿子,说是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能找上个媳妇,就下了东北,中间曾给回来过一次,专门表示了一下孝心,买了两包“到口酥”的点心给“愣大仁”吃了,接着又走了,从此没有再回来。“愣大仁”在62岁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一个又下着大雪的夜里,“愣大仁”来到了小黑的门前,在那儿站了很久,他是想推门进去的,但又没有敢进去,便在小黑家东屋山头上靠着墙角蹲下了,在天亮的时候,人们发现“愣大仁”已经冻死了。村里人把小黑从家里叫出来,叫他抓紧安葬了。那小黑却说:“死了,就死了是的,俺不管。”大队干部找到小黑,对他说要是不管,不抓紧埋了,就整死他,让他蹲牢去。这小黑害怕了,才从家中墙旮旯里扯出一领破席子,把“愣大仁”的尸体卷巴起来,用地板车拉着,拉到“东舍林子”挖了个坑埋了。外村一个常上我村讨饭的叫“马大”的人,打听到掩埋“愣大仁”的地方,趴在掩埋“愣大仁”的土堆上,整整哭了一个上午走了,也从此不来我村讨饭了。在“愣大仁”死后的第二年夏天,小黑在雨后的夜里,去西大沟边上的别人家菜园子里偷摘茄子,在慌乱中,失脚滑进大沟里淹死了。人们都说:“活该,该死,遭报应了。”
“愣大仁”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些人的人性的善与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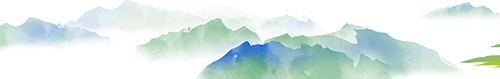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如果你也受够了“鸡蛋焦虑”,想给孩子、给家人一份真正放心的营养——
选鲜峰地标的无抗富硒可生食鸡蛋:
有出口备案的底气,有科学养殖的匠心,更有让你咬下第一口就惊艳的鲜。
(现在下单,京东快递当天发,4分钟锁鲜技术锁住蛋香,收到还是鸡窝里的温度~)
礼盒装54元到手30枚,京东包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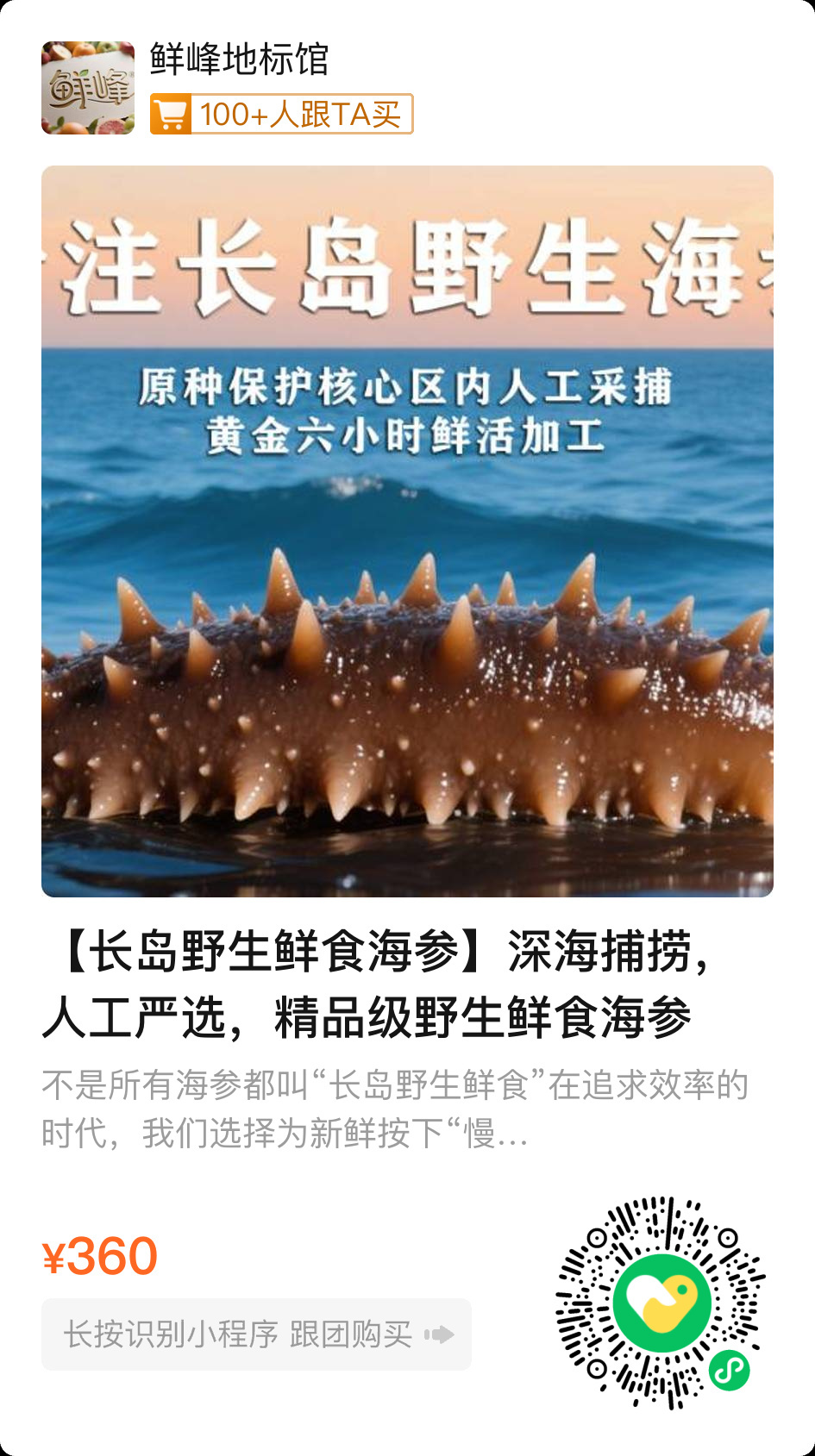
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