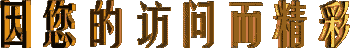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连载八
谣言的罪过
作者:尹玉峰(北京)
野姜花白,白不过云秀老师的粉笔灰
野姜花香,香不过赵麻杆儿的焦麻雀
驼子说“擦枪走火”,药瓶说
“奥美拉唑”;风一吹,姜花
低头,像云秀绞着手指的沉默;爸爸
的镐头劈开井沿,劈不开谣言的罪过
1
晨雾如乳白的绸缎缠绕着长白山余脉,将起伏的丘陵晕染成水墨画卷。露珠在柞树叶上滚动,折射出碎钻般的光芒,野蔷薇的清香混着松脂气息在晨风里浮动。布谷鸟的啼鸣穿透薄雾,惊起桦树林中一群山雀,扑棱棱的翅膀搅动着初夏的空气。
麦田铺展成起伏的金色海浪,麦穗低垂着饱满的籽粒,在阳光下泛着琥珀光泽。垄沟间,山民弯腰查看墒情,锃亮的锄头偶尔惊起草窠里的野兔。远处的玉米地已没过膝盖,叶片宽大如剑,在风中沙沙作响,与近处摇曳的黄豆苗谱写着绿色的二重奏。
山涧挣脱了残冰的桎梏,欢唱着奔下石崖,在青石板上撞碎成千万颗水晶。溪边,柳树的新枝蘸水梳妆,水芹菜顶着白花在浅滩摇曳。偶尔有狍子低头饮水,倒影被涟漪揉碎,又缓缓聚拢。雨后,蘑菇如褐色小伞在腐叶间悄然撑开,散发潮湿的泥土芬芳。
夕阳为群山勾勒金边时,缕缕炊烟从红瓦房顶升起,与晚霞缠绵。场院里,为了尝鲜,抢收籽粒开始灌浆,变得饱满,但又没有成熟的小麦,碾磨的面粉散发着暖香,妇女们忙着蒸制新面馒头。孩子们追逐着掠过草甸的萤火虫,犬吠声惊飞了归巢的乌鸦。远处传来山地马车的吱嘎声响,满载着希望的种子驶向待播的田野。
小满一过,山坡上的果园便成了鸟雀的盛宴。家雀儿蹦跳着啄食草籽,蓝点颏在枝头抖擞羽毛,红点颏的叫声清亮得像山涧流水,苏雀和黄雀则挤在野葵花盘上争食,三道眉的褐羽在阳光下泛着铜光。它们各自忙碌,互不打扰,偏是人类的算计比鸟鸣还聒噪。
赵麻杆儿蹲在田埂边,手里攥着几根马尾毛,正专心致志地编着套子。他的手指粗糙而灵活,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曲子。已经勒住几只家雀儿的细腿,那些小生命在套子里扑腾,发出细弱的叫声。他麻利地裹上泥巴,丢进火堆,火光映着他那张“做梦娶媳妇——想好事儿” 的脸,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
“给云秀带去,就说……就说我新打的。”赵麻杆儿搓着烟灰指头,眼神飘向村小学的方向,那眼神里带着几分羞涩,几分期待,仿佛云秀是他心中那朵遥不可及的野姜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让他心驰神往。
赵驼子从柴垛后闪出来,脖子一拧,脸上的皱纹像老树皮一样皱在一起:“云秀她爹是啥人?能瞧上你这点麻雀肉?趁早跟张红过日子,别折腾!”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眼神里满是算计和嘲讽。
赵麻杆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眼神变得黯淡无光。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套子,心里涌起一股委屈和愤怒。他喜欢云秀,喜欢她的温柔、她的学识,觉得她就像山间那清新的野姜花,与众不同。可父亲却总是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感情,让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狐仙门前过,无喜必有祸……”赵麻杆儿踢着石子嘟囔,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绝望。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像这脚下的石子,被随意踢来踢去,没有方向。突然,一股冲动涌上心头,他抄起顶门棍往院外冲,仿佛要去寻找那渺茫的希望。
赵驼子一把拽住他:“发啥癔症!”他的力气很大,像一只老鹰紧紧抓住猎物。赵驼子看到云祥福正扛着镐头路过,眼神一转,露出狡黠的光芒。他掏出怀里的双联璧硬塞过去:“亲家!这玩意儿配你正合适!”
云祥福愣住,眉头紧皱,眼神中满是疑惑和警惕:“谁是你亲家?”他的声音冷硬,带着一种天生的威严。
赵驼子咧嘴一笑,黄牙缝里挤出话:“你家云秀和我家小子,那可是青梅竹马!全村谁不知道?”他的笑容里满是虚伪和算计,仿佛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话音未落,云祥福已把玉砸回他怀里:“呸!你命里带‘子水’,克妻败家,还想拖我闺女下水?”他的声音如雷霆般炸响,眼神里满是愤怒和厌恶。他想起自己独自抚养云秀的艰辛,想起那些因为赵驼子一家而起的闲言碎语,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
赵驼子挨了骂却不恼,反倒凑近低语:“老哥,等云秀肚子显怀了,你求我接盘都来不及!”他的声音低沉而阴险,眼神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说着,转身就走,嘴里还故意哼着小调,一副胜券在握的得意样。
云祥福站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脑子里乱成一团。他抬头望向村小学的方向,心里又急又怒:“不行,得找云秀问清楚!”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赵驼子那得意的笑容和那些恶毒的话语,仿佛有一把钝刀在慢慢割着他的心。
2
云祥福三步并作两步往村小学赶,镐头还攥在手里,路上的村民见他这副模样,纷纷避让。他脑子里嗡嗡作响,赵驼子的话像毒蛇一样盘踞在心头——“吐酸水”“血气方刚”“擦枪走火”——这些字眼烧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他想起云秀小时候,那乖巧的模样,那明亮的眼睛,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情?可赵驼子的话又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无法平静。
“云老师,有人找!”一个学生在教室门口脆生生地喊。
云秀正在黑板上写作文要点,粉笔在她手中流畅地书写,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抬头看见父亲铁青着脸站在教室外,手里的镐头闪着冷光。她心里“咯噔”一下,粉笔从指间滑落,在地上断成两截。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又努力镇定下来。
“爸,您怎么……”她的声音带着一丝疑惑和担忧。
“出来!”云祥福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声音冷硬得像石头。
操场边的老槐树下,云秀绞着手指。她今天穿了件宽松的浅蓝色衬衫,微风轻轻拂过,带来一丝清凉。云祥福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刮过女儿的腰身,呼吸越来越重。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和愤怒,仿佛在审视一个罪犯。
“赵驼子……”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换了个说法,“你最近身子不舒服?”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那是愤怒和担忧交织的结果。
云秀先是一愣,继而突然笑出声来。这笑声让云祥福愣住了,他看见女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药瓶:“爸,我这是胃病又犯了。上周带毕业班摸底考,连熬三个晚上批卷子……”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无奈和疲惫,眼神中满是委屈。
药瓶上“奥美拉唑”四个字明晃晃的。云祥福突然想起,女儿打小就有胃病,初中时还因为熬夜读书吐过血。他握镐头的手松了松,”不行,我得找赵驼子算账去!”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愧疚,但很快又被愤怒所取代。
云祥福攥着药瓶大步流星往赵家走,镐头在身后拖出一道浅浅的痕迹。路过小卖部时,几个打牌的村民抬头张望,又赶紧低下头假装专注牌局——谁都知道云家当家的脾气比炮仗还爆。他们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畏惧和好奇,仿佛在看一场即将上演的闹剧。
3
赵家院门大敞着,赵驼子正蹲在井台边磨镰刀,见云祥福杀气腾腾地闯进来,三角眼一眯,慢悠悠站起身:“哟,云老哥,这是……”他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挑衅和得意。
“啪!”药瓶砸在井台上弹起老高。云祥福一把揪住赵驼子汗衫前襟:“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闺女是胃病吐酸水!”他的声音如雷贯耳,眼神中满是愤怒和坚定。
赵驼子脖子一缩,却瞥见药瓶上“奥美拉唑”的字样,嘴角竟扯出一丝冷笑:“胃病?老哥,这药是治胃酸,可云秀那晚在河边吐得昏天黑地,可不止是胃酸那么简单……”他故意压低声音,浑浊的眼珠里闪着算计的光,“村里谁不知道,姑娘家身子虚了,多半是……怀了!”他的声音像毒蛇吐信,让人不寒而栗。
云祥福的拳头“砰”地砸在井台边,青石裂开一道细缝:“放屁!我闺女是老师,是正经人!”他的额角的青筋暴起,像一条条扭曲的扭曲的蚯蚓,镐头“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溅起几粒泥星。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仿佛在捍卫自己最后的尊严。
赵驼子却像没听见似的,慢条斯理地擦着镰刀:“老哥,你急啥?麻杆儿昨儿还跟我说,云秀答应他等秋收后成亲。你想想,一个姑娘家,大半夜往河边跑,还吐得那么厉害,不是怀了是什么?”他故意拖长语调,镰刀在石头上磨出刺耳的“滋啦”声,“再说了,云秀那件蓝衬衫,最近是不是总穿?宽松了,怕遮不住肚子吧?”他的声音里满是嘲讽和挑衅,仿佛在欣赏云祥福的痛苦。
云祥福的呼吸越来越粗重,胸口像塞了块烧红的炭。他想起女儿最近总说身子乏,饭量也减了,难道……赵驼子的话像毒蛇一样钻进他脑子,啃噬着他的理智。他猛地转身,镐头“唰”地抽出,寒光直逼赵驼子咽喉:“再敢胡说,老子今天就要你命!”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意,仿佛要把赵驼子撕成碎片。
赵驼子却笑了,笑声里带着一股阴冷:“老哥,你砍我容易,可砍得了村里的闲话吗?前儿个李婶还跟我嘀咕,说看见云秀在河边蹲着,手捂着肚子,脸色白得像纸……”他故意停顿,眼神扫过云祥福颤抖的手,“你闺女要是真清白,怎么不找麻杆儿对质?反倒躲着你?”他的声音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云祥福的自尊。
云祥福的镐头“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他踉跄着后退两步,后背撞在井台边,冰凉的石头激得他打了个寒颤。赵驼子的话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他的自尊——他一个光杆司令,养大的闺女,难道真被赵麻杆儿那混小子糟蹋了?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仿佛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云老哥,别冲动。”赵驼子慢悠悠走近,镰刀“啪”地插进土里,“这事儿,得慢慢来。等云秀肚子显怀了,你求我接盘都来不及!”他拍了拍云祥福的肩膀,力道轻得像羽毛,却压得人喘不过气,“到时候,麻杆儿娶你闺女,我赵家给你养老送终,多好的买卖?”他的声音里满是算计和虚伪,仿佛在描绘一幅虚假的美好画卷。
云祥福的拳头攥得咯咯响,却一拳砸在空气里。他抬头望向村小学的方向,那里传来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像针一样扎进他耳朵。他想起女儿在黑板上写字的模样,粉笔灰落在她肩头,像一层薄雪——那样的姑娘,怎么会……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仿佛在怀疑自己的教育方式。
“赵驼子!”他嘶吼一声,转身冲出门外,镐头在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扭曲的痕迹,像一条挣扎的蛇。他的脚步沉重而急促,仿佛要去寻找一个答案,一个能让他从这痛苦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答案。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