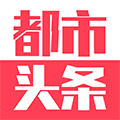城步县三十六峰的雪
作者 苗乡樵夫
城步的冬天,是慢慢来的。先是风里带了刃,削得杉木的叶子一片片往下掉;接着是溪水瘦下去,露出青黑的脊背;然后,在某一个你未曾留意的清晨,推开门,那三十六峰,便白了头。
说是雪景,其实最先到的,不是雪,是静。一种铺天盖地、沁入骨髓的静。往日里那些鸟鸣、松涛、溪涧的碎语,都被一种柔软而浩大的东西吸了去,沉入山峦浑圆的梦里。空气是清冽的,吸一口,像含了一块薄荷冰,直凉到肺腑深处,却又带着林木与冻土最本真的气息。你站在那里,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埃,又仿佛因分享了这天地间的静穆,而变得无限充盈。
看那山峰罢。它们不再是夏日里那般蓊郁苍翠、棱角分明的模样了。雪是一位最高明的画家,用的却只是最素净的笔。它并不刻意覆盖,只是轻轻柔柔地,依着山脊的走势,顺着岩壁的纹理,一片一片地敷上去。向阳的坡面,雪便薄些,露出底下深黛的、赭石的底色,像是巨人衣衫上泼洒的水墨;背阴的壑谷,雪便积得厚实丰腴,白得那样纯粹,那样安稳,仿佛已沉睡了千年。三十六峰,此刻便成了三十六位披着素氅的仙人,有的凝神独立,有的并肩私语,在氤氲的、乳白色的寒气里,影影绰绰,似真似幻。
近处的景致,却又是另一番玲珑天地。屋瓦的楞角钝了,茅草的檐口肥了,都裹着一层毛茸茸、亮莹莹的雪边。最动人的是那些树。杉树挺直了身子,墨绿的针叶托着一条条蓬松的雪,像是精心缀着的流苏;落了叶的灌木丛,则成了千万只毛茸茸的、蜷着的小兽,静伏在坡上。偶尔,“扑”的一声,是竹枝承不住那沉甸甸的白,微微一倾,便滑下一大捧雪末来,纷纷扬扬,在寂静的阳光里,闪着一瞬即逝的、细碎的银光。那雪落下的声音,轻极了,也空灵极了,像是这静穆世界里唯一被允许的叹息。
山脚下,苗寨的木楼静卧着。青黑的瓦脊镶了宽宽的白边,吊脚楼下的石阶,一级一级,也被雪衬得分明。炊烟起来了,是极淡的、灰蓝的一缕,袅袅的,不急不缓,升到那一片无边的白与静里去,便也分不清是烟还是雾了。寨子里少有行人,只雪地上几行疏疏的脚印,深深浅浅,通向溪边,或没入另一片木楼。那脚印也安静,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你忽然觉得,这雪不仅落满了山,也落满了时间,让这寨子,连同其中缓慢的生活,都成了琥珀里温存的风景。
若说白日里的雪峰是庄严静默的哲人,那黄昏时分,它们便成了温柔的诗人。西边的天,透出些冻玫瑰似的、极淡的霞色来,羞怯地,不敢浓烈。那光便匀匀地抹在群峰的雪冠上,给那无瑕的白,染上了一层极薄极暖的、蜜似的莹润。山岚渐起,丝丝缕缕,从谷底漫上来,像仙人舒卷的衣带。群山的轮廓在暮霭里渐渐柔和、模糊,最终与苍茫的天色融为一体。寒意骤然深了,砭人肌骨,可心里,却无端地生出一种熨帖的暖意来。
夜,是真的来了。没有月亮,天是幽深的蓝黑,而三十六峰的影子,却比天色更沉,静静地蹲踞在视野的尽头。雪地映着微光,是一片朦朦的、清冷的白,仿佛大地自身在呼吸,在吐纳着一种亘古的微芒。万籁俱寂,你几乎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听见时间如雪粒般,沙沙地从指缝间溜走。
忽然想起古人的句子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此情此景,何其相似。可在这里,在这城步的三十六峰之间,你感觉到的并非孤绝,而是一种被接纳的安宁。那雪,覆盖一切,也连接一切;它冷却了世界,却仿佛焐热了人心深处某个柔软的角落。它让你知道,天地可以如此广大,又如此慈悲;岁月可以如此苍茫,又如此静好。
这一场雪,是山峦一场盛大的冬眠,也是天地一幅留白的长卷。而我,只是一个偶然闯入的逗点,有幸在此驻足,呼吸,然后,带着一身清冽的雪气,悄悄地,退回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