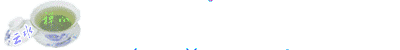从苦难中绽放的诗性:论余秀华诗歌的生命书写与当代文化启示
作者:墨染青衣
近年来,中国当代诗坛因“贾浅浅现象”引发了一场关于诗歌底线、审美标准与文化责任的激烈论争。高秀群女士在《清扫一切文化垃圾,让中国文化回归正位——从贾浅浅的屎尿诗说开去》一文中,以犀利的笔锋批判了当下诗坛中存在的低俗化、口水化、功利化乱象,痛斥那些“假、丑、恶”的作品对“真、善、美”文化传统的亵渎。文中列举的“平安经体”、“羊羔体”、“废话体”、“下半身体”等,被指认为脱离现实、空洞无物、甚至粗鄙下流的“文化垃圾”。这场讨论在网络与文艺社群中激起广泛回响,如在《当代文艺》作者群内,社长陈顺灿(寒风)旗帜鲜明地支持抵制低俗,强调平台应“传播正能量”,乔世苓、吕晓蓉等老师亦对缺乏诗情画意、不堪入目的作品表达了强烈反感。这场讨论的核心,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当代中国,诗歌乃至文学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应当承载何种价值?仅仅以“打破禁忌”、“实验创新”为名,是否就可以无视基本的美学规范与道德底线?
然而,在“清扫垃圾”的呼声与对低俗作品的批判浪潮中,另一个名字被反复提及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余秀华。群内讨论中,星海、墨舞飞、吕晓蓉等作者明确将余秀华与贾浅浅之流区隔开来,认为余诗“有内涵”、“高于当代诗坛的很多人”,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大胆的夸张写法”,而非低俗的欲望宣泄。傅维敏老师更系统地介绍了余秀华身残志坚的历程与“情感真挚浓烈”、“意象独特新颖”、“语言质朴有力”的创作风格,指出其诗是“带着血与泪的生命之书”。这不禁引人深思:同样涉及身体、欲望、日常甚至苦难的书写,为何余秀华的诗歌不仅未被归入“文化垃圾”,反而被广泛认可、引发深刻共鸣?她的创作实践,能否为走出高秀群女士所批判的困境,为“让中国文化回归正位”提供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启示?本文旨在深入剖析余秀华诗歌的艺术特质与精神内核,探讨其作品如何在直面个体生命残缺与苦难的同时,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力量与人性光辉,从而为当代诗歌创作与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值得深思的参照系。
余秀华的诗歌之所以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首先根植于其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脑瘫带来的行动不便、口齿不清,乡村生活的封闭与困顿,婚姻中的不幸与压抑,共同构成了她个人命运的“深渊”。然而,她的诗歌绝非对苦难的简单陈列或顾影自怜。与高秀群文中批判的某些作品耽于展示“丑恶”以哗众取宠不同,余秀华的书写是一种将苦难彻底内化后的艺术转化。她的诗中,身体之痛与存在之思紧密交织。
在《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中,她写道:“我身体里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这里的“火车”是一个极具独创性的意象,它既是饱受疾病困扰、行动不便的肉身,又是承载着各色人生、穿越时间轨道的生命本身。“斑驳”道出了残缺与沧桑,“不慌不忙”却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包容与承受力。疼痛不再是单纯的被动忍受,而被转化为一种主动的、近乎献祭般的“取悦”,其中蕴含着对命运复杂而悖论式的接纳与对抗。这与那些单纯描写生理器官或排泄物以刺激感官的“下半身”写作,有着云泥之别。余秀华将身体的局限,升华为观察世界、体验存在的独特棱镜。
她的抗争哲学,集中体现在对爱情与自由近乎蛮横的渴望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所以引发轰动,并非因为标题的直白,而在于其内核的纯粹与强烈:“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这里的“睡你”,早已超越生理层面,成为一个汇聚了全部生命力、对抗整个生存荒芜与时空阻隔的终极行动符号。“枪林弹雨”、“黑夜”象征着现实的重重障碍与内心的无边孤寂,而“穿过”、“摁进”、“奔跑”等一系列极具力度的动词,则喷薄出一股原始而悲壮的生命意志。这种渴望,源于其现实情感生活的极度匮乏,因而更显其真挚与灼热。它不是在优裕中无聊的意淫(如沈浩波《一把好乳》中所流露的),而是在干涸沙漠中对一滴水的拼命追寻。余秀华的诗歌,因此成为她“摇摇晃晃”行走于人世间最稳固的精神拐杖,是她与不公命运谈判、甚至宣战的武器。她的“不雅”或“大胆”,背后是生存的严肃与尊严的呐喊,这与为标新立异而刻意粗鄙的创作动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余秀华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生命体验的独特性,更在于她将这种体验淬炼成了一套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诗歌美学。这与高秀群所批判的“废话体”、“梨花体”等仅将大白话分行、完全抛弃诗歌艺术建构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余秀华的诗歌意象主要植根于她熟悉的乡土中国。麦子、稻田、野花、村庄、月光、霜……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象,在她的笔下被赋予了鲜活的灵性与深邃的隐喻。例如,在《我爱你》中,“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将病中自我与“陈皮”并置,陈皮是晒干蜷缩的,带着苦辛的药性,却又在时光中沉淀出价值。这个比喻精准、朴素而奇异,将日常的枯燥、生命的苦涩与阳光的温煦奇妙地融合,透出一种隐忍的酸楚与淡然的宁静。她的意象选择与营造,始终紧扣其情感与思考,是内容与形式的自然契合,而非为了晦涩而晦涩,或为了堆砌而堆砌。
她的语言风格以质朴、直接、有力著称。她摒弃了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技巧,擅长用最日常的语言,撬动最沉重的情感与最深刻的存在之思。“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我爱你》)。诗歌在这里被谦卑地让位于更坚实的“植物”与“庄稼”,而“稗子”这个在农田里需要被剔除的“他者”,恰恰成了诗人自身命运最贴切的象征——“提心吊胆的春天”,道尽了边缘者生存的脆弱与惊惶。这种语言,具有刀劈斧凿般的直接性和穿透力,它不依赖任何文化噱头或姿态,而是凭借情感的真实与洞察的锐利直抵人心。
更重要的是,余秀华的诗歌在“泥土”(现实、苦难、日常)与“星辰”(梦想、自由、超越)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结。她从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与不堪,但又总能在其中发现诗意,仰望星空。她的诗是扎根于苦难大地,却始终向着精神天空生长的植株。这种美学建构,使得她的作品既具有坚实的现实感,又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实现了“接地气”与“有灵气”的统一。这与那些要么完全脱离现实、沉溺于空洞形式游戏,要么只会展览丑陋、缺乏审美提升的所谓“诗歌”,划清了界限。
回到高秀群女士引发的关于“文化垃圾”的讨论,以及《当代文艺》群内老师们对诗歌标准的关切,余秀华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答案:如何区分“真诗”与“伪诗”?如何在创新中不迷失诗歌的本真?
首先,诗歌的根基在于生命经验的真诚与深度,而非题材的猎奇或形式的乖张。余秀华写身体、写欲望、写疼痛、写乡村,所有这些题材都来源于她切肤的生命体验,并且经过了深刻的情感沉淀与思想过滤。她的“大胆”是生命内驱力的自然喷发,是“不吐不快”的真谛。而某些被批判的诗作,其描写屎尿屁、堆砌废话、模仿结巴,往往缺乏这种内在的情感与思想必然性,更像是为吸引眼球而刻意为之的“题材投机”或“形式表演”。前者是“为情造文”,后者易沦为“为文造情”,甚至“为噱头造文”。
其次,诗歌的创新必须服务于意义的生成与美感的营造,不能沦为空洞的语言游戏或底线挑战。余秀华的诗歌在语言和意象上确有创新,但所有这些创新都是为了更精准、更强烈地表达她的情感与思考。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创新的,但其力量来自意象组合所构建的庞大情感张力场。反观某些“废话体”,其“创新”仅仅停留在对诗歌分行这一形式的滥用上,剥离了分行,其文本作为散文甚至日常口语都信息匮乏、意义稀薄,这种“创新”实则掏空了诗歌的内核。
再次,诗歌应当具备将个体经验升华为普遍人类情感的能力。余秀华的诗歌虽然极度个人化,写的是她的残疾、她的爱情、她的村庄,但她所表达的对于爱、自由、尊严的渴望,对于命运的抗争,对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却能穿越个体的藩篱,引发广泛共鸣。读者在她的“稗子”里看到自己的“提心吊胆”,在她的“穿过枪林弹雨”中感受到自己为理想奔赴的勇气。而一些仅限于展示私人怪癖、低俗趣味或空洞能指的作品,则无法建立这种通往普遍性的桥梁,只能在小圈子内自娱自乐,或成为公众吐槽的对象。
最后,健康的文学生态需要严肃、理性、基于文本的批评。《当代文艺》群内的讨论,既有对低俗作品的明确拒斥,也有对余秀华作品的具体分析(如傅维敏老师的介绍),这体现了良好的批评意识。高秀群的文章虽有情绪化的表述,但其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一种现象和风气。对于余秀华,也存在不同声音,但讨论多围绕其作品本身展开。这正是文艺批评应有的态度: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而是就作品论作品,以美学和思想的尺度进行衡量。这有助于涤清浮躁之气,引导创作走向深入。
余秀华的诗歌,是在个人命运的残缺处,开出的精神之花;是在生活现实的尘土中,升起的灵魂之星。她的写作有力地证明:真正的诗歌,无关乎作者身份是否显赫(她并非“作协副主席”之女),无关乎题材是否“高雅”,甚至无关乎身体是否健全;它只关乎心灵是否真诚、感知是否敏锐、思想是否深刻、语言是否有淬炼生活与情感的力量。她以自身的实践,回应了高秀群女士对“真、善、美”回归的呼唤——她的“真”是生命体验毫不伪饰的袒露,她的“善”是对苦难的坚韧承受与对美好的执着向往,她的“美”是苦难在语言中结晶而成的独特艺术光华。
当下中国文坛,特别是诗歌领域,确需警惕高秀群所指出的种种“垃圾”泛滥的现象。那些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故弄玄虚、甚至以丑为美的作品,确实在污染着文化的空气。然而,在“清扫”的同时,我们更需思考何为“正位”。余秀华的道路启示我们:中国文化的“正位”,不是回到某种僵化的格式或虚伪的颂歌,而是回归到对真实生命的关切,对人性深度的挖掘,对汉语表现力的锤炼,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她的诗歌,既深植于中华土地与传统(对乡村、自然的深情),又洋溢着强烈的现代个体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普通、苦难与超越如何达成艺术融合的杰出范例。
因此,讨论余秀华,不仅是在评价一位诗人,更是在探讨当代诗歌乃至文学的一条可能路径:如何在喧嚣中保持沉静,在浮躁中深耕生命,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独特而坚实的声音。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抗文化虚无与低俗化的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那些源自生命最深处的真诚吟唱,永远拥有打动人心、照亮晦暗的力量。这或许才是“让中国文化回归正位”中最值得珍视的“正位”之一——即人的主体精神的站立与艺术表达的尊严。
附诗一首:
七律·咏余秀华诗魂
文/墨染青衣
身困尘泥志未残,心驰旷野笔如澜。
痛深翻作穿云箭,情挚凝成沥血丹。
稗子惊春吟世味,火车载梦越嶙峋。
摇摇晃晃人间路,一朵荆棘戴作冠。
【作者简介】
张龙才,笔名淡墨留痕、墨染青衣,安徽芜湖人,爱好文学,书法,喜欢过简单的生活,因为 简简单单才是真,平平淡淡才是福。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了过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懂得知足的人,即使粗茶淡饭,也能够尝出人生的美味!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