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让记忆看见我 (17首)
■钟磊(吉林)
▌为孤独正名
在至暗时刻过夜,
那是午夜零点使我睡不着,
在凌晨崩塌,连同我所仰望的星空和喧嚣时代,
好比是乌俄战争的疑云,
弥漫过三年记忆,也包括三年大疫。
此时,我的耳朵却是聋的,
被炮声和疫苗当成小厮,
在北中国的白夜写诗,记录下第聂伯河的忧郁,
也记录着黑龙江的涟漪,
是如此贴切在为孤独正名,
那是因为白银之光而与声光交织在一起。
按理来说,我只是安静生活的一个信号,
却不是,那么像被傀儡瘫痪在一张床上的僵尸,
横躺在黑暗的统治之中,
远不如一根枯树枝, 可以看见一只黑鸟结束白昼,
再将我粉碎成黑暗的两个齑粉,
完全是虚构的,完全是乌有的,
一个是空心的,
一个是灰色的。
2025/2/24
▌我不打算再看它们一眼
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
看不懂拉丁语的人在看电影,只是看剧情。
不说看电影的人吧,
如果我懂英语,那么我就会把英语翻译过来,
把电影制作成配音,
用听得懂的汉语洗耳朵,洗心,
那样,就会有人为我送上一瓶红酒,
用威士忌包装一个高脚杯,
以思想的嘴巴啜饮。
可以幻想在一个酒吧,
神明的幽辉,一直弥漫在一个半敞开式的包间中,
怡然自乐于古希腊式的幸福。
这样,也会让我的诗歌变得淡泊,
把乌俄战争,欧盟以及美国总统搁置在一边,
就像是排列好红、黄、蓝的词语,
让它们装饰好瓦西里·康定斯基三角形的三个斜边,
我不打算再看它们一眼。
2025/2/28
▌给时间改一个名字
而今,乌鸦的叫声带着乌克兰的口音,
落在了莫斯科广场上,
那是人间失格的信号,
在要求狐狸和猎人友好相处,并不打算埋葬谁?
实际上,莫斯科广场并非是椭圆形的,
被一种红色在十分钟之内挤爆,
那么像商人的睡眠,
在一个椭圆形的会议室里被吵醒,
突然,冒出吵架的味道。
那么像语言世界在给人泼冷水,
而两个椭圆形并不等于一滴眼泪,
使我陷入沉思,那是知识分子的无奈,
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进入诗歌,给时间改一个名字。
再把2025年 3月3日当成偶数,
在比对语言的成色,在分辨着乌鸦的口音,
那么像一个没有抱负的诗人,
在以卑微的生命,试图模糊掉语言的边界,
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2025/3/3
▌一如诗歌所求
最终我将死去,也不可能重生,
让灵魂歇一歇吧,
罢了,切记。
我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月亮就陨落了,
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守夜人,也是我的梦,
只是孤独的样子,
因为担心成就不了自己而屈从于生活,
必须得干活,请记住:“至死也不能死在床上,
或故意在死亡中逗留一小会儿。”
我总是在凌晨三点半钟起床,
一如诗歌所求,在一个黑房子里寻找窗户,
可以大舒一口气,看见了日出,
又被阳光晒透,又看见了飞舞的麻雀或蝴蝶——
嗯,那些黑暗的词,那些迷茫的词,
也从我的身体上一片片脱落,
正如月亮和镜子。
2025/3/14
▌异域的孤独
为此,我获得了终生流放,
正在北中国的沼泽地上跋涉,像一首诗。
难道我不是艺术的主题?
难道庸碌的心智不是垂死者的面容?
一连串的追问是如此两难,
那么像词语不等于语言,摆脱不了异域的孤独,
更糟糕的是我弄不清楚自己,
更不是完美之物。
的确,我必须要绝地反击,
如果把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泔水灌进自己的肚子,
那么肠胃就会打结或长出息肉,
将横躺在一张病床上,会变成鬼迷心窍的一个人,
迷恋上一个小灵魅,
或闯入一片墓地在为那个小灵魅叫好。
或与一俱腐尸相同,穷于一种荒秃的生活,
过着惶惶不安的日子,
要不世界是一个聋子,
要不我是自己的哑巴。
2025/4/10
▌代数学的一个公式
碰巧,我的青春与一个传说重叠,
时而诡谲,时而类似于一场赴死,
那么像代数学的一个公式。
忽然,代数学被拆分成两个单页那么像吕贵品和我,
他去了天堂,并坐在一把空椅子上,
轻摇起一把折扇,那是我为他做的,
那里有百姓与山河,
也有他的一首诗,犹如我熟悉他的悲伤,
犹如他对我说出的希望。
后来,我变成了心照不宣的暗语,
流亡在被流放的汉语中,不逊于一颗赤子之心,
在以天真的真理饱蘸着一滴滴血汁,
抄录着未竟之账的原作,
在真实之处见证真实,在拒绝非人之说。
真正的二十世纪,已经点数出邪恶的总和,
使我觅得道德诗篇,犹如在二十一世纪空间上的并置,
呼应着毁灭之灾,
即是真实的言说。
2025/4/25
▌可怕的契约
以五·一劳动节的名义休息,要我称颂吗?
是下意识的吧,
要我一把抓住控制论,
从一本书里拧出汗水,
哦,一滴汗水比银河中的一颗星星还要浩渺。
(那是沉默的国家,并不知道我的忧愁。)
于是,惊诧在迅速移动,
已经越过名词,又浮起水晶一般的线条,
那是伸展在半空上的灵魂,
使得每一种黛青色都是私人的耳语。
噢,我在兑付可怕的契约,
在让苦难的门徒懂得血液结痂成过去的名字,
耻于道德的伪装,耻于星空的传说,
将再生于伊曼努尔·康德的仰望中,
将化作我的出身和摇篮,在流亡的汉语中流亡,
像集中营中的一个伪劣写手,
在合心镇的星期日忙于火车的制造工作,
也忙于落日时分的裁决。
2025/4/30
▌自由出入的未来
乌克兰的马克西姆·克里夫佐夫诗人牺牲了,
他的生命却在诗中发芽,
像紫罗兰,再把世界染成紫红色,
这是坏血统吧,盛开在地狱一季。
不可能的,诗的光芒在渐渐代替黑夜,
那是神圣之光,在一架钢琴键上敲打着命运的节拍,
穿过黑暗的灌木,从灌木的顶尖露出未来,
又转向自由出入的未来,
那也是我对坏血统的提问,
那是他在把地狱的火焰看做一种慰藉吗?
随后又是扑灭火焰的泪滴吗?
嗅一嗅在其中夹杂的硝烟味,
迅速变幻的场景,几乎是诗人们担当的相同角色,
让我从一场落难中把自己选出来,
在一场得救的幻觉中做一个通灵人,
区别于动物或野兽,在抛弃另外一些人,
在喊:“去吧,魔鬼。”
2025/5/18
▌让记忆看见我
兀自现身的食人兽,吞掉了仅有的一个白昼,
又在一座黑雕像中睡去,
使得言之无物的黑夜无法结束。
是谁颁布了禁言令?
在把俄语变成汉语,又把汉语变成英语,
两种语言的流亡,第一次是到达意大利,
开始说起日瓦戈医生,
像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选边站,
被迫放弃一个奖项,
说起1960年5月30日的一件事儿,
说起该死的人被时间俘虏了,又把快乐说过一遍,
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
那是流亡的汉语到达北中国,
是啊,我在用汉语重构时间和语言世界,
想把2025年5月30日变成一样的,
把我放在隐喻里,配得上返璞归真,
比光的骤雨还要快,没有什么能够让我置身其中,
没有对称的坟墓,
让记忆看见我。
2025/5/30
▌在骇人的真实中隐藏寓言
在世上,再也没有羡慕的人,
都是羞于为人,
这是一首诗的引子,也是一个人的流亡史,
说出来是如此荒谬。
现在,我深陷在汉语的集中营中,
已经耗尽了我的半生,
开始断言我的后半生仍是流亡,
如同把汉语说成拉丁语,宁愿作为语言世界的明证,
堪称真实:那些刽子手,奴隶贩子。
若想拆除苍蝇的翅膀,那么就要拆除交缠的欲望,
在骇人的真实中隐藏寓言,
真的,我没有任何隐讳,
像伯特兰·罗素那样在揭人短,在等不幸自行消退,
我怎么会屈从于同类相食的诱惑?
怎么会是其中的一个人?
我是有救的,将是最后一个人,
将是从汉语集中营中逃走的一个人。
2025/6/4

▌以一个人呼应另外一个人
六月的禁言令,连接着幽灵的驱使,
使我不能写诗,说诗歌里的内容,包括有毒的汉语,
使我为自己的软弱而羞愧。
为何不可理解?因为我厌恶有毒的汉语,
就像保罗•策兰厌恶德语一样,
宁可承受痛苦和不幸,
也不想做被德语任意摆布的一个人,
以一个人呼应另外一个人,
做一个诗人吧,哪怕是难上加难。
我明白,我虽然是证人的证人,
但是,六月的存在只是让阳光在雨水中嬉戏,
紧接着又把阳光溺毙于一池水中,
看啊,那些人的脸色都是平布纹,几乎都是一个版本——
而我在记录六月的最后一天,
用稍纵即逝的诗行界定自己,
那是作为一个诗人活过的自画像,那是一种光线变化,
像被雨水打湿的长发,在一池雨水中跳荡起来,
并不是理发师要修剪的那一种——
2025/6/30
▌不必用手抄本回忆我
早晨,风中的音乐流入耳鼓,
那是从头顶滑落在脚底,
恰似有两个音符被自己的废墟掩埋,
即是让我颤抖两次,一次是疼痛在第六根肋骨上,
一次是把时间堆在61号公路边上,
来不及让我细数一遍。
是的,恐怖的战争布满了我的身体,
使我在接受诘问:“为什么呼吸着黑色的空气?”
这样,反而封缄不了我的舌头,
一如我将诗篇赠予未来,
只是在抽屉里呐喊,只是隐藏着一把空椅子的边界。
不,请不必用手抄本回忆我,
请把词语用对,包括音乐和写意的影像,
在这世上没有一座灵魂的旅馆,
没有,什么也没有——
2025/8/26
▌未知的艺术家
对贪婪者待以仁慈,这是在午夜所读的诗,
这是安妮•塞克斯顿的告解书。
是的,那是未知的艺术家伫立在时间之上,
像时间的水平轴或垂直轴,
在把我带回信仰,使我加入时间内部,
并在左肋骨上留有裂痕,留有疼痛的呼吸。
而我却不能赞美空气,
虽然可以在午夜中央仰望星星,
但是,黑眼睛的疼痛还是比黑暗的天空大一些儿,
那么像钟表上的子夜集中营,
让我的黑眼睛无法吸附它,
让我见过从未比黑暗更加黑暗的事物——
是的,在黎明餐厅的稀饭吧中,
只有一张鸡蛋饼是水平的,却又偏向于失败的一边,
又偏爱上公道的悲剧——
2025/9/4
▌被明亮的谎言说明
在累人的高处,我的忧郁像一朵星云,
在你喜欢的黑暗中,
像世界的真相隐而不见。
看啊,不需要你惊讶,
我的孤独就是在精神荒原上的一盏孤灯,
被明亮的谎言说明,
在死亡的黎明中冲撞着死亡,
几乎是难辨的符号,像信仰的重负之物,
已经与张志新和张展相似。
而我不需要明天的审判,
只是一个缪斯,在让暴怒的嘴巴像世界的洞穴和深渊,
埋葬掉被谎言驯服的真相,
死给真相看,如你的枯燥忏悔不能救赎自己,
如我看你的时候就想到窗户,
就想到玻璃监狱。
2025/9/18
▌还有这种事吗
是的,我不会说匈牙利语,
而弗朗茨•卡夫卡会说,
那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兹洛也会说,
证明我得到了匈牙利语的力量。
有人说:“匈牙利语和德语及俄语没有亲戚,
那么像拉丁语的异类。”
而在灾难和恐怖时代,
这种富有远见的语言表述,使我不应该感觉陌生,
于是,我在反抗忧郁,
在排弃汉语之毒,从合心镇开始洗心,
让盐碱地的第一个雨滴落下来,
之后在秋天里结霜,类似与汉语之毒唱反调的人,
类似被大萧条冻醒的人,
在说:“还有这种事吗?
从此被修订的仁慈关系被翻译成瘾,
在与汉语变得密不可分,
因此,有人在打听我在哪儿?”
2025/10/10
太阳像早晨的借口,说着古怪的想法,
类似于米兰·昆德拉的主题,
一个男人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
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眼睛,
而自己的眼睛并不是天空的眼睛,令人惊讶。
此刻,我已经失智,
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早晨的片段一共是半小时,
肯定了艺术家的耳朵,
甚至说是语言世界的蜗居。
于是,我听到了辰时五点的钟声开始阐述,
事先说起家庭巢穴发生的事儿,
一切都带有沉默的色彩,
仿佛是嫁接的语言世界,在分岔的时间上渐行渐远,
无论说什么都不会被说出来,
只有我随着语言的移动说起该死的自己,
或去追赶别的事物。
2025/10/21
今天是秋天的劫数,仿佛生物没有了生殖,
被一个冬天的冷冻结了,
让恐怖成为冰天雪地的反光。
不必等到四季轮回,可以写一写立冬的日子,
那么像革命或政变的街头巷议,
反而坦言地说不是背叛。
忽然,我发现菜市口与谭嗣同的告别,
败落的不止是菜市口大门,还有市民走过去的默然无觉,
没有一张嘴巴在向他认错,
包括菜市口一带的万家灯火。
是啊,辛亥革命的纪念碑那么像是自吹自擂,
只相信未来的愚蠢之物,
反而使得不受怀疑的词源学没有上限,
总是得逞于历史光辉的盲目之白,
却以灾祸著名。
2025/11/6
▌难以启齿的对话
那样的话,必须用耳朵错过它,
正如弗朗茨•卡夫卡那么像一只甲壳虫,
让我一时语塞。
是啊,让我的耳朵静止下来,
让语言失去重量,
而失重的语言带着病症总是在人间失格,
那么像难以启齿的对话。
此刻,危险的匈牙利语又说起撒旦探戈,
几乎是直抵黑暗中心,
又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兹洛将我带回应许之地,
几乎是最危险的敌人,
在把流亡的汉语当成诅咒,
在说:“让有毒的汉语在黑暗中心转一转,
我虽然无法分辨出语言的气味,
但是活着有毒的符码正在变成永恒的黑暗之轨。”
而我只想丢下这种本事,
接下来说:“你甭对我说了。”
2025/11/14
▌寒衣节所见
看啊,我的灵魂从汉语的牢笼里逃出来,
感觉到寒衣节的寒冷,
却被一个女子发现,
那是该隐之印使我在人间失格,
又使我纵身跃入未知。
呀,她却在我的灵魂所归之地叩问我是谁,
她又把我称为seIf,
她又朝着早晨光明而清澈的方向望过去,
于是,我走出自己的躯壳,
在以枯萎的芦花点缀真理,
也把眼睛称为大海在说:“把太阳融入大海。”
而在此刻,我试图谈起形而上的太阳,
无需滴血认亲,也无需冷却或热烈,
正如心灵地图的终极奥义,都是栩栩如生的PERSONA,
正在把太阳凝望成一面镜子,
却挽不回时间,只是得见于明日之我仍然是我,
习惯于笨拙的扭曲——
2025/11/18
▌如歌的行板
心疼,像被打入一个肉钉子,
正在冬天里缩成一团,再做失败的一纸传单,
以讲故事的样子来塑造我们,
那么像如歌的行板。
像我愿意像切斯瓦夫•米沃什那样,
在虚构的时间里活过两次,
和我一起细察自己的真实,
准备学习狐狸的技艺,
并在思考女人的丰腴叙述,
把九尾狐穿上加重的皮靴,从冰天雪地上穿过,
又加入雪花的多声部合唱,
像我们在重复着无花果的因果。
而我羞于说出拯救不了人民的诗歌是什么,
此刻,我紧盯着鱼尾纹的藏身之处,
寻找着从前的你,你却在一道涟漪中迅速散开了,
算得上美学的坚强和安慰,
却使我如此致命。
2025/12/4

▌诗人小传
别怕重复,我已经是死亡的风景,
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里跌入黄昏,
却没有人为我祈祷,
只是经过沃罗涅日的彼得大帝雕像,
惊起一片乌鸦,又让我的头发变成一片银白。
嗯,黑色的森林在北中国的暴风雪中呻吟着,
比北方狼的嚎叫瘆人,
此时的我并不是荒原狼的哪一种,
只是在极目流放地的寒冷与空阔,
却用恐怖的眼皮躲闪,让流亡的汉语顺着嘴唇褪色,
像在抄袭诗歌,像冬天的程序。
别说我在复制灵魂,我早已经闻到了血腥味,
那是汉语的集中营也把我的骸骨整取成零,
或把我从弯曲的地平线上轰走,
或在零的下方陷入虚构的裂痕,
那么像一具没有被安葬的尸体——
2025/12/6
▌死亡之日
是啊,我是心怀苦涩的一个人,
独自在暮色中哭泣,
而陪伴我的一只花猫正在死去的风景中控诉,
在扑捉一个灯泡的弧线,
那个灯泡刚好是破碎夜晚的痂斑或龌龊,
像黑色的乱伦和腐败。
如果我说什么话都没有用,那么就沉默吧,
静静地与一个夜晚平行,
放下思想淫荡的一件事儿,放下学习一束光的意义,
让死亡从死亡的身体上经过,
让死亡决定我去哪儿。
那儿就是死亡之日,在充当幽灵的第二手稿,
或用佛罗那安眠药来干一些反常事儿,
或以魔鬼招来恶之转化,
仍把我当成临终前的一个玩偶,
仍把我当成诗歌的一个鬼才。
2025/12/8
▌私下流传
天啊,是这么惊人,
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和我一起跨入未知之地,
愿意依偎在我的身旁,
被北中国的诗歌认为相同,一起拄着诗歌的拐杖。
没错,这是私下流传,
结果是宣称我们陷入汉语的流亡,
姑且像整个大地的孤寂,
在把我放在舌尖上炙烤,
让我想到自杀的剧本是如此丢人,
像有人在自己吓唬自己,在以旧身体代替自己。
哦,在那里有我的自画像,
更需要剪窗花的一个手艺人,
或剪开我们,或使我们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近乎是写作的低谷,并不适合于一个故事的伦理,
正如我嗅入她的味道,
并念及她的哀伤,仅留下祈祷——
2025/12/9
▌说得够多
甚至要重新叙述,
要把上帝给予的天赋,毫无保留地献给人间。
当然,这样说没有错,
这是一首诗的第一行,试着穿过天堂之门,
接下来,用一朵白云见证,
像有人在推算用300张羊皮印制一部圣经,
或等待一次性地完成名人志。
换一个词吧,谁也不能代替耶稣,
那是白云的痕迹,最后也是雨水的晚熟,
在让知更鸟飞过贫穷的起点,又被各种名字填满。
并非是出于信念,那么像狭小的英雄主义,
既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
是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兹洛也不是纯粹的人,
在反问自己,这惊人的生物是谁?
突然,让我也冒出一个念头,
所以我说得够多,让所有人都站在人妖的边界线上,
一起结束人类的丑闻。
2025/12/10
▌好似一个答案
在年末写诗,好似一个答案,
让诗人在轮流值守,
让我停止在冬天的边缘,
又大喊一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而我不是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
仍把汉语楔入骨殖,
也把受伤的双手捆绑上绷带,
并耷拉在向晚的天色中,
竟然像把荒蛮的冰雪塞给了流放地——
不,西风已经来了,
我在把雪莱,P.B和W.H奥登当成时间的长条纹,
丢下日常的词汇,在离开前世,
当然是把一头狮子和一头老虎当成伙伴放在这儿,
在把冬天和春天一起描述,
一定有火焰般的颤抖,一定有诗人的破折号,
可以戳破白色的修辞,
在2025年12月10日星期三,
让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就坐。
2025/12/10
▌无人之地
我犯下了人的罪行,
辜负了人,即在进入无人之地,
从来也不是人的答案,
恰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可以是人的答案。
好呀,别说我在断章取义,
我在与孤独签下一纸协定,
像宿命让我隐遁,也在让所有的人都一样,
除了自知,已不是他物。
我不再接受黑白的交替训练,不再为爱撒谎,
要以爱收场,要收走人的风干器。
此时,我在拒绝等待我的人,
正在鄙视偶然的相逢,又苦煞成人的最后一局,
更不想告诉谁,我是谁,
我成就了谁,正如无我之死——
2025/12/11
▌慷慨的回应
难以对付的失眠,在暗夜里出卖我,
不是遥远的星光,
甚至不是被感知的凄然,只是临终前的训导。
是啊,从心脏造影的褪去开始,
主动脉一直处于麻木状态,
或只是这个样子,等于一年的一半,
被分配在冬天的暴风雪中,并固定在不毛之地,
仿佛是流放地的一垄垄犁沟,
被置放在我的前额。
但是,我还在慷慨的回应,
如同用两簇肩火在撬动一座冰山,
使我明白,一个小巧而光滑的白色头骨在整夜漂浮着,
犹如从一个妇女的嘴中喊出来,
总是觉得什么都不够用,
像没有餐桌、没有厨房、没有谷仓,
也没有情人亲吻那样——
2025/12/12
▌一个幸福的果报
请允许我抄袭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次,
那是他写给安娜·斯维尔的诗,
“我想,我是爱上她了,
尽管我们不是恋人,但可以通过共情感受到她的身体。”
不,这不是诗歌标本,
也说服不了蝴蝶,我要从时间的坟墓上迁徙,
放弃随风动摇的人,脆弱的人,
在说:“我在建筑爱情艺术。”
如果严冬的铁脸仍是冰冷的,
那么我也想在阴霾中偶然一见,仅以智慧的孤寂证明,
一个幸福的果报,带着嫉妒的折磨,
避开了红色日出的漂洗,
恰如蝴蝶花最想做的,如梦一般坠入前世。
是啊,那一夜的疼痛入骨,
封锁了荼蘼的荒径,恰似人间四月天抵得过四季流转,
只是片刻种下的菩提树,
只是微笑描定的爱情样式。
2025/12/12
▌荒诞的叙述
一把空椅子,在去往天堂的大路中央燃烧着,
并没有让人感到堵塞,
只是发现了自己的叹息和惊恐,
那么像崇祯皇帝上吊的事儿,
那么像闪光的丝绸,
几乎是深入到冬至的前夜,
正在抵达冬天的边缘,在为最短的时间哀戚,
却讲不出裸体发光的原因,
仍在追问:“我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
不,那是死亡的语言,
在用汉语点数着语言的死亡率,
又杀死了接近真相的一些人,
在把人变成相似的生物,
都是面包屑的主人,在上演生物学的皮影戏,
充满了动物的忍耐气息,
宁愿变成荒诞之物的隐喻,也不愿意做二手时间的证人,
只是荒诞的叙述,在贪婪的舌尖上烂掉。
2025/12/19
▌猜一猜
冰冷的诗歌总是偶遇冬天,
正如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的日子,
等于不可理解的风景,
正在雨夹雪的天气预报中返回北中国的流放地。
此时,我的诗歌像一只铁鸟,
正在穿越天空的铁笼,尚未找到什么答案,
与意象大师无关,比天空的白云洁净,
是何等的快乐,阿门。
没事,正是人生的主题,
可以使我永远远离黑暗,然后是一个破折号,
在以写诗的荒诞,战胜不写诗的荒诞,
在以不荒诞的语言,战胜荒诞的语言,
可以路过塞满乱石和荒草的天空,阿门。
好吧,我能够为之死去,
让身体加入燃烧的火焰,也不介意被说出什么,
猜一猜是飞蛾,还是蝴蝶,
猜一猜是笑翠鸟,还是知更鸟,
随便吧——
2025/12/19

钟磊的诗
呼啸的刀锋,从不惧怕疼痛的风声|钟磊:让记忆看见我(17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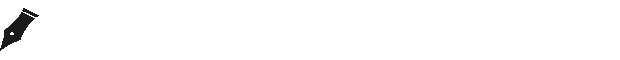


钟磊,独立写诗数十年。著有《钟磊诗选》《信天书》《圣灵之灵》《空城计》《失眠大师》《孤独大师》《意象大师》《活着有毒》等诗集,诗集被郑裕彤东亚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


我在简阳等你,我在春天等你|宇风 步钊 林兰英 巫英 周敏诗抄
何房子:“我始终站在世界的对面”——喻言口语诗歌写作的开创性和先锋意义
——更多佳作请点击顶部“中国新诗天地”关注后查阅历史消息欣赏。

中国新诗天地

诗意视野,写意人生
四川简阳市作家协会 主管
《新诗天地》编委会 編輯
顾问:黎正光 宇风
主编:步钊 林兰英
编辑部主任:郭毅
编委:步钊 林兰英 郭毅 李茂鸣
陈小平 王学东
邮箱:zgxstd@163.com
长按二维码识别关注

微信号:zgxswk


以上内容为用户自行编辑发布,如遇到版权等法律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官方客服,平台会第一时间配合处理,客服电话:18749415159(微信)、QQ:75770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