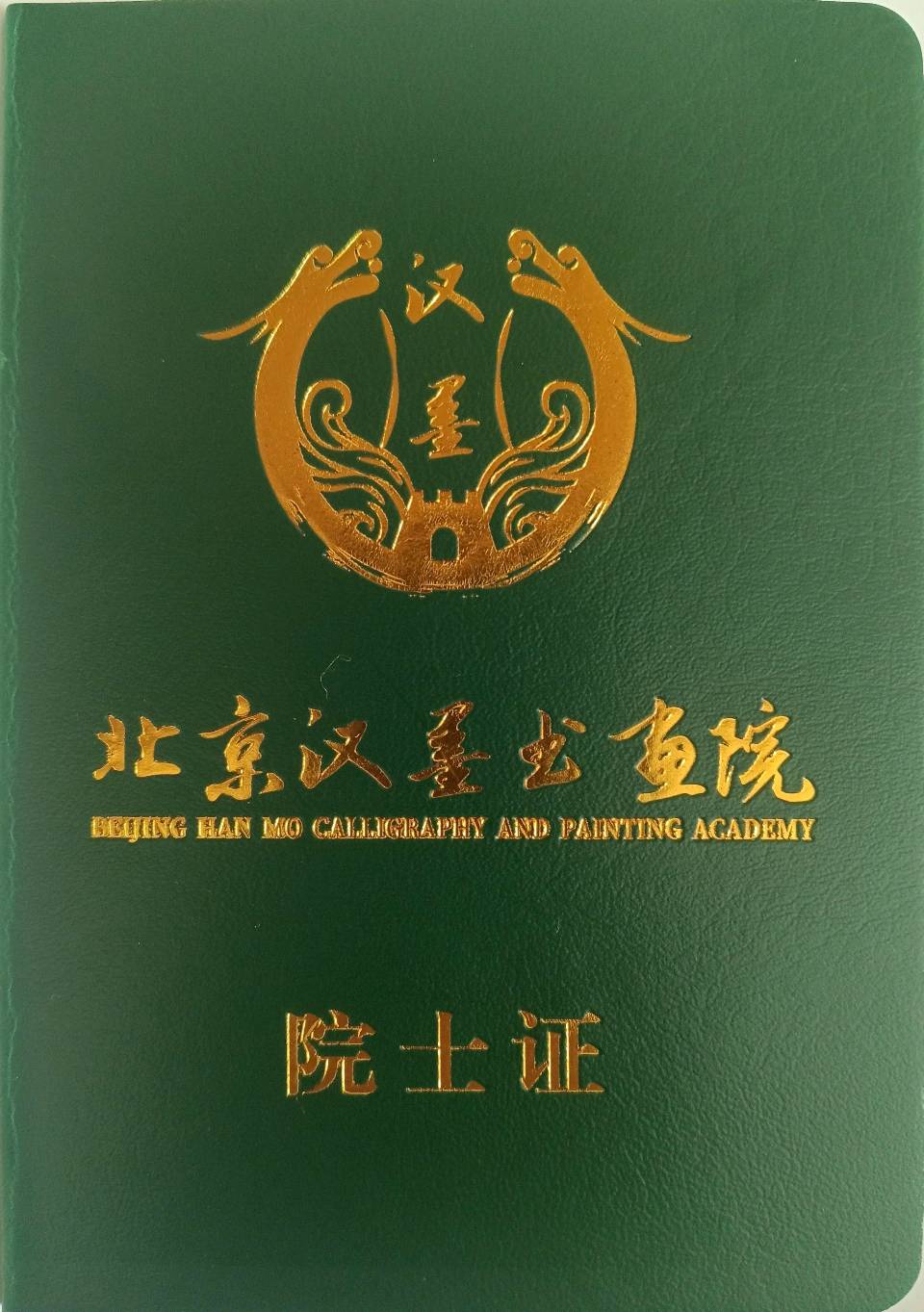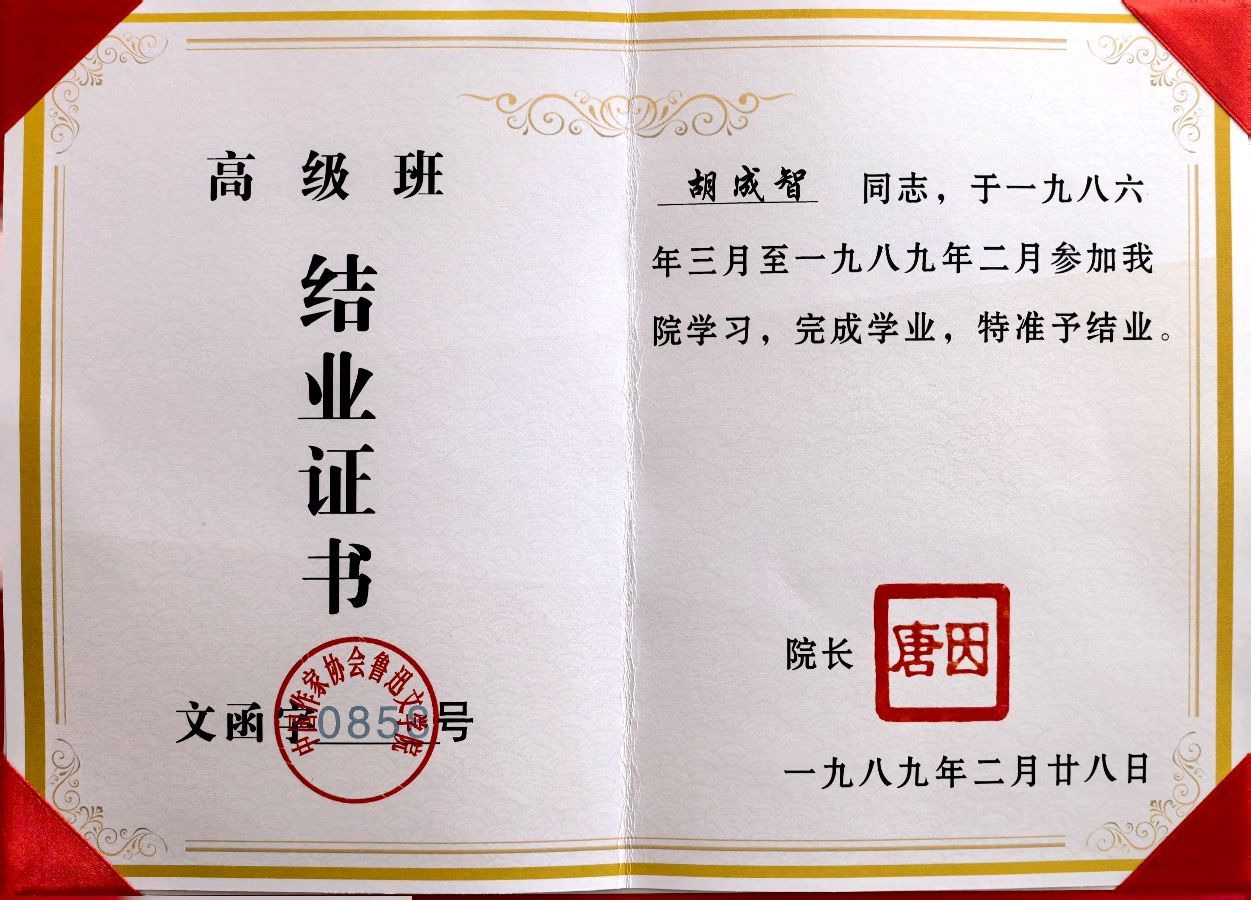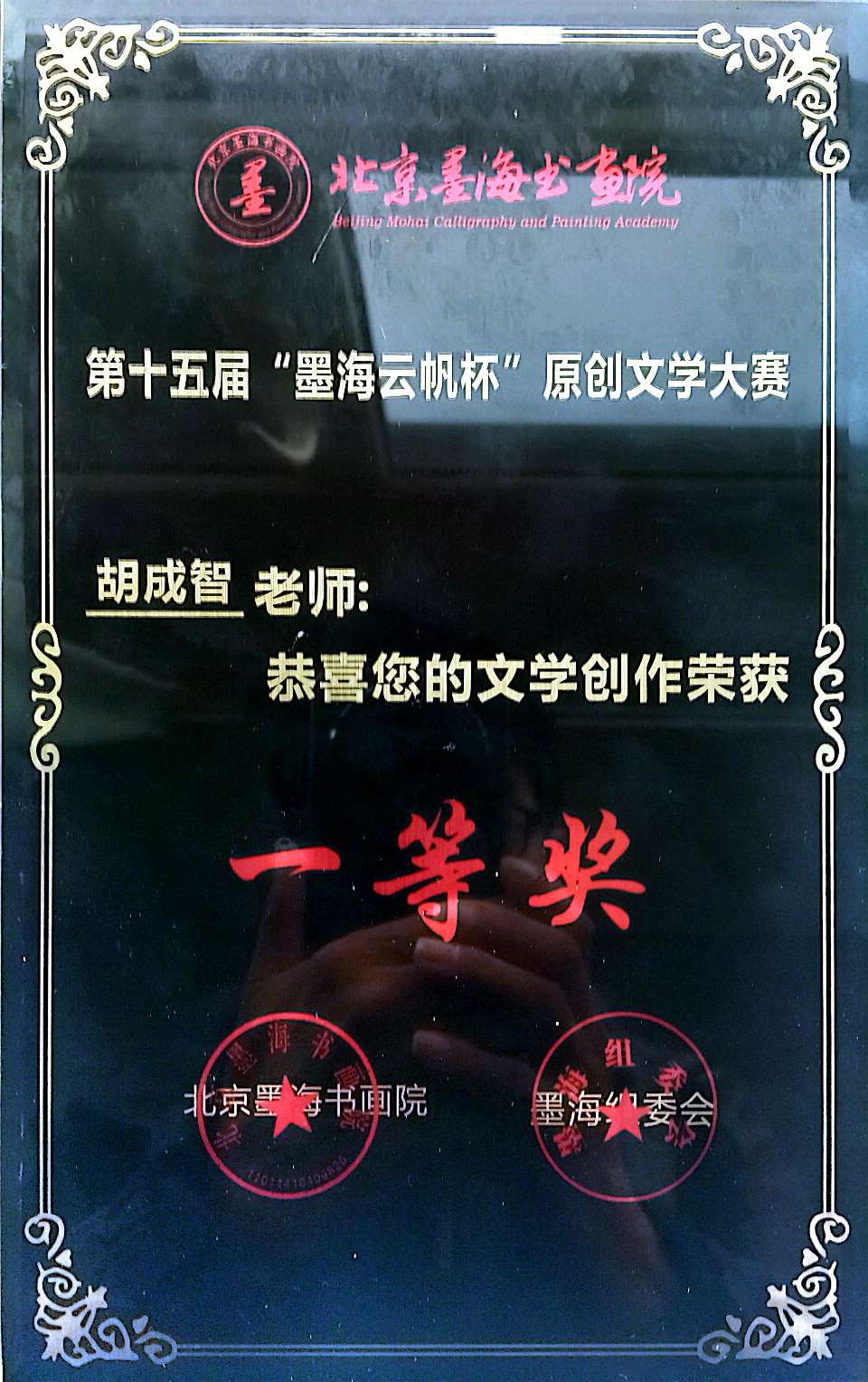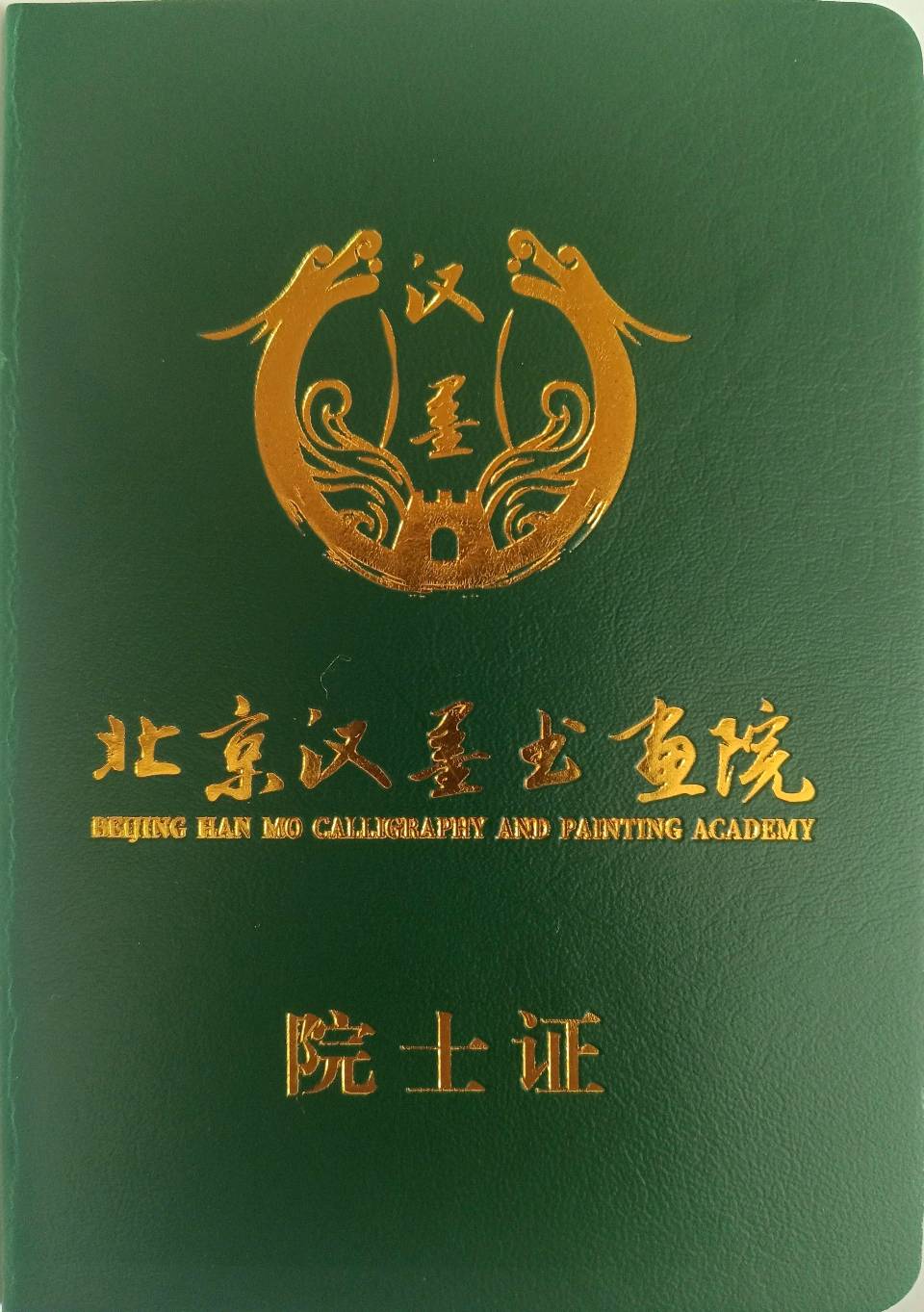第九章 孤帆
江风裹挟着冰凉的雨丝,横掠过宽阔的江面,发出呜呜的声响,如同万千冤魂在齐声哀泣。沈家那支由三艘破旧货船和两艘勉强加固过的渔船组成的小小船队,此刻正像几片微不足道的枯叶,在浑浊翻涌的波涛间剧烈地起伏、颠簸。
沈文谦紧紧抓住主船船舷上一根冰冷的、满是铁锈的栏杆,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他的长衫下摆早已被甲板上的积水和雨水彻底浸透,沉甸甸地贴在腿上,每一次船的晃动,都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但他浑然未觉,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那莽莽苍苍、仿佛永无尽头的雨幕和水道。
离港还不到一个时辰,林家那庞大船队的帆影早已消失在视线之外,连最后一点模糊的轮廓都被这天地间的混沌彻底吞噬。此刻,在这浩瀚的江面上,仿佛只剩下他们这一支渺小、孤独而又不合时宜的队伍。
“呕——”
身后传来压抑不住的呕吐声,那是女眷和年幼的孩子。狭窄的船舱里挤满了人,空气污浊不堪,混合着舱底积水的腥气、桐油味、以及晕船呕吐物的酸腐气息。每一次剧烈的颠簸,都引来一阵惊恐的低呼和无助的啜泣。
沈知白脸色苍白地从船舱里钻出来,踉跄着走到父亲身边,扶住另一根栏杆,才勉强站稳。他强忍着胃里的翻江倒海,哑声道:“父亲,舱里……情况不太好。母亲头晕得厉害,小侄女一直在哭闹,怕是受了风寒。”
沈文谦没有回头,目光依旧锁在前方,声音被风吹得有些破碎:“让……让大家坚持住。用我们带的生姜,切碎了泡点热水喝下去。书箱……书箱怎么样?”
“都用油布盖着,也用绳索固定了,暂时无碍。只是这船……”沈知白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脚下这艘吱嘎作响的旧船,“吃水太深,我怕……”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沈文谦明白。这几艘船本就是临时拼凑,为了装载这些沉重的书箱,已然超载。此刻在风浪中,每一次起伏都显得异常笨重和艰难,仿佛下一刻就会散架,或者被一个稍大的浪头打翻,彻底沉入这冰冷的江底。
就在这时,船身猛地向一侧倾斜,一个巨大的浪头扑上甲板,混浊的江水哗地冲刷过来,瞬间淹没了他们的脚踝。沈文谦和沈知白死死抓住栏杆,才没有被甩出去。船舱里顿时响起一片惊恐的尖叫。
“稳住!大家抓牢身边的东西!”沈文谦用尽力气高喊,但他的声音在风浪面前显得如此微弱。
船工们在前艄声嘶力竭地呼喝着,调整着那面破旧风帆的角度,与风浪搏斗。他们的脸上也写满了紧张,显然,这样的天气和江况,对于这几条超载的旧船来说,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沈文谦的心,随着船身的每一次剧烈摇晃而悬起、落下。他不再去看那迷茫的前路,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脚下那被油布严密覆盖的书箱。那里面,是文天祥批注的《守城录》,是苏轼的手札,是沈家十数代人的魂。这些冰冷的、无声的纸张,此刻却仿佛有了千钧重量,不仅压在船上,更压在他的心头,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做出的这个“与书共存亡”的决定,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更将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拖入了这场巨大的、吉凶未卜的险境之中。一种沉重的负罪感,如同这冰冷的江水,瞬间浸透了他的四肢百骸。
“父亲,我们会……会没事的,对吗?”沈知白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毕竟还年轻,面对这天地之威和渺茫的前途,恐惧是本能。
沈文谦转过头,看着儿子苍白而写满依赖的脸。他看到儿子眼中映出的自己——一个同样狼狈、同样恐惧,却必须强作镇定的老人。他深吸一口冰冷的、带着水腥味的空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
“天地之大,总有我辈容身之处。只要书在,人在,希望……就在。”
这话像是在安慰儿子,更像是在说服自己。他抬起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心中默念:“列祖列宗在上,若沈文谦此举有违天意,所有罪孽,我一人承担!只求……只求护佑这些无辜的家人,护佑这文明之火,不至熄灭!”
风,更急了。雨,斜斜地抽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孤帆远影,在莽莽苍苍的江天之间,艰难地向着不可知的未来,一点一点地挪动。
第十章 抉择
林家庞大的船队,此刻正以相对平稳得多的速度,航行在主航道上。与沈家小船队的挣扎相比,他们显得从容而有序。坚固的船体有效地抵御着风浪,训练有素的水手们各司其职,船帆吃满了风,推动着船队破浪前行。
主船的船长室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江上的寒湿。林慕云已经脱去了湿重的蓑衣,换上了一件干爽的丝棉长袍,坐在铺着厚厚毛皮的檀木椅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参茶。但他并没有喝,只是怔怔地看着杯中袅袅升起的热气,目光没有焦点。
船长室外,风雨声被厚实的木板隔绝,显得遥远而模糊。室内一片寂静,只有炭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以及他自己有些紊乱的心跳声。
沈家那支渺小、狼狈的队伍,如同一个无法驱散的幽灵,在他脑海中反复浮现。他看到沈文谦站在雨中那单薄而执拗的身影,看到那些破旧船只不堪重负的吃水线,看到在风浪中惊恐万状的女眷和孩童……这一切,都像一把钝刀,在他良心上反复切割。
他清楚地知道,以沈家那几条船的状况,在这越来越恶劣的天气里,能顺利抵达第一个预定补给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大的可能,是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江段,被风浪吞噬,或者因为船只故障而搁浅、倾覆,最终葬身鱼腹,而那些他们视若性命的书籍,也将随之沉入江底,永不见天日。
这个念头让他坐立难安。
“父亲。”林焕章推门进来,他脸上带着航行顺利的轻松,“按照现在的速度,天黑前我们应该能到达青龙咀,在那里避一夜风浪,明日一早再继续南下。”他走到桌边,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一饮而尽,“还是咱们的船好,要是指望沈家那种破船,怕是早就……”
“焕章!”林慕云猛地打断了他,声音有些严厉。
林焕章愣了一下,看到父亲阴沉的脸色,意识到自己失言,讪讪地住了口。
林慕云放下茶杯,站起身,走到舷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江面。雨水在玻璃窗上划出一道道扭曲的水痕,如同他此刻纠结的内心。
救,还是不救?
理智告诉他,不能救。调头回去,寻找不知已偏离到何处的沈家船队,不仅会耽误宝贵的航行时间,增加整个船队遭遇未知风险的概率,更可能因为搭载沈家和那些“敏感”的书籍,而引来占领区势力的注意和追查,将林家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他是林家的家主,必须为这几百号人的身家性命负责。
可是……道义呢?那几十年的交情呢?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老友一家,因为自己的“见死不救”而走向毁灭?沈文谦守护的,难道仅仅是沈家的私产吗?那些典籍,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根脉啊!自己今日若袖手旁观,他日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午夜梦回,又如何能心安?
两种念头在他脑中激烈地厮杀着,几乎要将他撕裂。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太阳穴突突地跳动着。
“父亲,您……还在想沈家的事?”林焕章小心翼翼地靠近,低声道,“我知道您念旧,可……可事已至此,我们无能为力啊。就算我们现在调头去找,这茫茫江面,雨大浪急,如何找得到?说不定他们……他们早就……”他没敢说出那个不祥的词,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更何况,”林焕章继续道,语气变得凝重,“我们肩负着林家复兴的重任,船上还有这么多跟着我们、指望我们的人。我们不能为了一个……一个渺茫的可能,拿所有人的命运去冒险。父亲,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儿子的话,像一记重锤,敲打在他摇摆不定的天平上。是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是林慕云,是商海沉浮几十年,以决断力著称的林慕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优柔寡断了?
他猛地转过身,脸上所有的挣扎和痛苦都在一瞬间收敛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他走到书案前,案上摊开的,正是那份详细的南下计划和航线图。
他的手指,重重地按在了代表“青龙咀”的位置上。
“传令下去,”他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冰冷得如同窗外的江水,“全队保持航速,按原计划,前往青龙咀锚泊避风。”
“是!父亲!”林焕章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立刻躬身领命,快步退了出去。
船长室里,又只剩下林慕云一人。
命令已下,再无转圜的余地。他仿佛亲手斩断了最后一根可能连接沈家的绳索。
他缓缓坐回椅子上,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参茶,一饮而尽。那冰冷的、苦涩的液体滑过喉咙,一直凉到了心底最深处。
他闭上眼,靠在椅背上,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惫。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灵魂深处涌上来的、无法排遣的倦怠。
窗外,风雨声似乎更急了。
第十一章 迷途
雨,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反而愈发狂暴起来。豆大的雨点砸在江面上,激起无数混乱的水花,使得整个视野都变得模糊不清。狂风卷起浪头,一个接一个地砸向沈家那支弱小得可怜的船队。
沈文谦所在的主船,发出了令人牙酸的“嘎吱”声,仿佛下一刻就要解体。船舱里,呕吐声和哭喊声已经微弱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寂般的绝望。人们紧紧抓着身边任何可以固定的东西,面色惨白,眼神空洞,仿佛已经接受了即将到来的命运。
“老爷!不好了!”一个浑身湿透、脸上带着惊惶的老船工,连滚带爬地冲到沈文谦面前,声音带着哭腔,“舵……舵叶好像被水里的暗桩或者杂物撞坏了!船……船不受控制了!”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船身猛地一个剧烈的、毫无规律的扭动,几乎将甲板上的所有人都甩飞出去。
“什么?!”沈知白失声惊呼,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沈文谦的心,也猛地沉了下去,直坠冰窖。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这茫茫大江之上,船只失控,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能修吗?”他强自镇定,抓住老船工的手臂,急切地问道。
老船工绝望地摇了摇头:“这风浪太大,水下情况不明,根本没法查看,更别说修了!而且……而且我们好像偏离主航道很远了,这地方水情复杂,暗礁也多……”
他的话像是一道死刑判决。
失去了控制的船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风浪的裹挟下,开始漫无目的地漂流、旋转。另外两艘货船和渔船,试图靠近救援,但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自身难保,几次尝试都险些相撞,只能眼睁睁看着主船被风浪越推越远,消失在浓密的雨幕和波涛之中。
绝望,如同这无边的江水,彻底淹没了沈文谦。他看着家人们那写满恐惧和无助的脸,看着那在颠簸中死死固定的书箱,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攫住了他。
他错了么?他为了守护这些文明的象征,却要将活生生的人带入死地?这究竟是坚守,还是自私?
“父亲!看!那边……那边好像有个河汊口!”沈知白突然指着左前方,声音因激动而尖锐起来。
在迷蒙的雨幕中,隐约可见江岸在此处出现了一个缺口,形成一条看似相对狭窄平静的支流河口。
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一个可以暂时摆脱风浪、寻找地方抢修船只的机会!
“快!想办法把船往那边靠!用桨!用篙!什么都行!”沈文谦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嘶声喊道。
幸存的水手和还能动弹的男丁,纷纷拿起船上一切可用的工具,拼命地划水、撑篙,试图在这失控的状态下,勉强调整方向,朝着那个河汊口靠拢。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拔河。每一次努力的效果都微乎其微,风浪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船只在原地打着转,时而被推近河口,时而又被拉回狂暴的江心。
沈文谦的心,也随着这忽近忽远的距离,时而提起,时而落下。他不再去思考对错,不再去担忧未来,所有的精神都凝聚在这唯一的目标上——进入那条支流!
不知过了多久,仿佛是他们拼尽全力的挣扎感动了上天,又或者仅仅是幸运女神的偶然一瞥,一股奇异的回流,裹挟着失控的船只,猛地将其推向了那个河口!
船身剧烈地一震,撞开了河口处丛生的芦苇和浮木,歪歪斜斜地冲入了那条相对平静许多的支流。
速度骤然减缓,颠簸也明显减轻。甲板上的人们,几乎虚脱地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仿佛刚从鬼门关爬回来。
但危机并未解除。船只依旧失控,顺着支流的水流,向着未知的、幽深的腹地漂去。两岸是茂密的、在雨中显得黑沉沉的芦苇荡和模糊的树林,看不到任何人烟。
他们暂时逃离了江上的风浪,却闯入了一片更加迷茫、充满未知的境地。
沈文谦扶着栏杆,望着眼前这条仿佛没有尽头的、被雨雾笼罩的陌生水道,心中没有丝毫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更深沉的忧虑。
书,暂时保住了。人,也暂时安全了。
可前路何在?另外几条船上的家人是否安好?他们现在何处?
这一切,都没有答案。
迷途,不知归处。
第十二章 锚地
青龙咀,是一处位于大江转弯处的天然避风良港。当林家庞大的船队依次驶入这片相对平静的水域,下锚停稳时,几乎所有悬着的心都落了下来。
风雨在这里威力大减,只有细密的雨丝依旧无声地飘洒,落在船帆、甲板和幽暗的水面上。各条船上开始升起炊烟,食物的香气混合着雨水的清新,渐渐驱散了航行带来的紧张和疲惫。
主船的船长室内,灯火通明。林慕云坐在桌前,面前摆着几样精致的小菜和一壶温好的黄酒。林焕章坐在他对面,正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抵达南方后的商业蓝图。
“父亲,到了那边,我们可以先利用带去的资金和机器,重建纺织厂和五金作坊。那边原料便宜,劳动力也充足。而且,我打听过了,那边洋行多,我们可以直接跟洋人做生意,把我们的丝绸、桐油卖出去,利润比在内地高得多……”
林慕云默默地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呷一口杯中的黄酒。酒是上好的绍兴花雕,温热醇厚,但他喝在嘴里,却感觉不到丝毫滋味。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窗外那一片漆黑的、代表着来时方向的江面。
沈家的影子,如同鬼魅般,始终缠绕着他。
他试图用儿子的雄心壮志来麻痹自己,试图用林家光明的未来来说服自己,他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一个家主责任的。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拷问:你真的尽力了吗?你真的连尝试寻找一下都没有,就判了他们死刑?
“父亲,您是不是累了?”林焕章察觉到父亲的心不在焉,停下了话语,关切地问道。
林慕云放下酒杯,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沙哑:“没事,你继续说。”
林焕章犹豫了一下,还是继续说道:“还有,到了地方,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得尽快跟当地的士绅和官员打好交道。乱世之中,没有靠山,生意做得再大也是空中楼阁……”
就在这时,舱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压低的交谈声。过了一会儿,大副推门进来,脸上带着一丝凝重。
“老爷,少爷,”大副行了礼,低声道,“刚才后面‘福顺号’的瞭望手报告,说在入港前,好像隐约看到下游偏西方向的江面上,有微弱的火光闪了几下,像是求救的信号。但距离太远,风雨又大,看不真切,很快就消失了。”
舱内的气氛瞬间凝固了。
林焕章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风雨这么大,看花眼了吧?说不定是雷电的反光,或者是哪条渔船的灯火。不必大惊小怪。”
大副看了一眼林慕云,见他沉默不语,便躬身道:“是,少爷。可能是看错了。”说完,便退了出去。
舱门重新关上。
林焕章转过头,看着父亲瞬间变得异常难看的脸色,心中了然。他叹了口气,语气放缓了些:“父亲,我知道您心里放不下。但那种情况下,一点微弱的、不确定的火光,能说明什么?就算……就算真是沈家,我们现在又能做什么?调集船队,冒着夜航和风浪的危险,去那片不熟悉的水域寻找?这太不现实了!我们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林慕云没有说话。他缓缓站起身,走到舷窗边,推开了一小道缝隙。冰冷潮湿的空气立刻钻了进来,带着江水的腥味。他望着窗外无边的黑暗,那黑暗浓稠得化不开,仿佛能吞噬一切。
那微弱的、一闪而逝的火光,如同沈文谦最后投来的那道目光,虽然遥远,却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
他知道儿子说得对,理智上完全正确。回去寻找,希望渺茫,风险巨大。
可是……
他仿佛能看到,在那片无尽的黑暗和风雨中,沈文谦和他的家人,正站在一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点燃了最后的希望之火,而那火焰,却被自己这边的人,以“不现实”、“风险”为理由,轻易地忽略了。
一种巨大的、无法排遣的悲哀和负罪感,如同这青龙咀夜晚的寒气,丝丝缕缕地渗透进他的骨髓里。
他关上舷窗,隔绝了外面的寒冷和黑暗,也仿佛隔绝了内心最后一点软弱的挣扎。
他转过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对林焕章说道:“不早了,你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
林焕章看着父亲那平静得近乎麻木的脸,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行了个礼,退出了船长室。
林慕云独自一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桌上的酒菜早已冰凉。他走到床榻边,和衣躺下,闭上了眼睛。
然而,他知道,今夜,注定无眠。
锚地的寂静,只能衬托出他内心惊涛骇浪的回响。那莽莽苍苍的江雨,不仅困住了迷途的沈家,也永远地,困住了他的灵魂。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