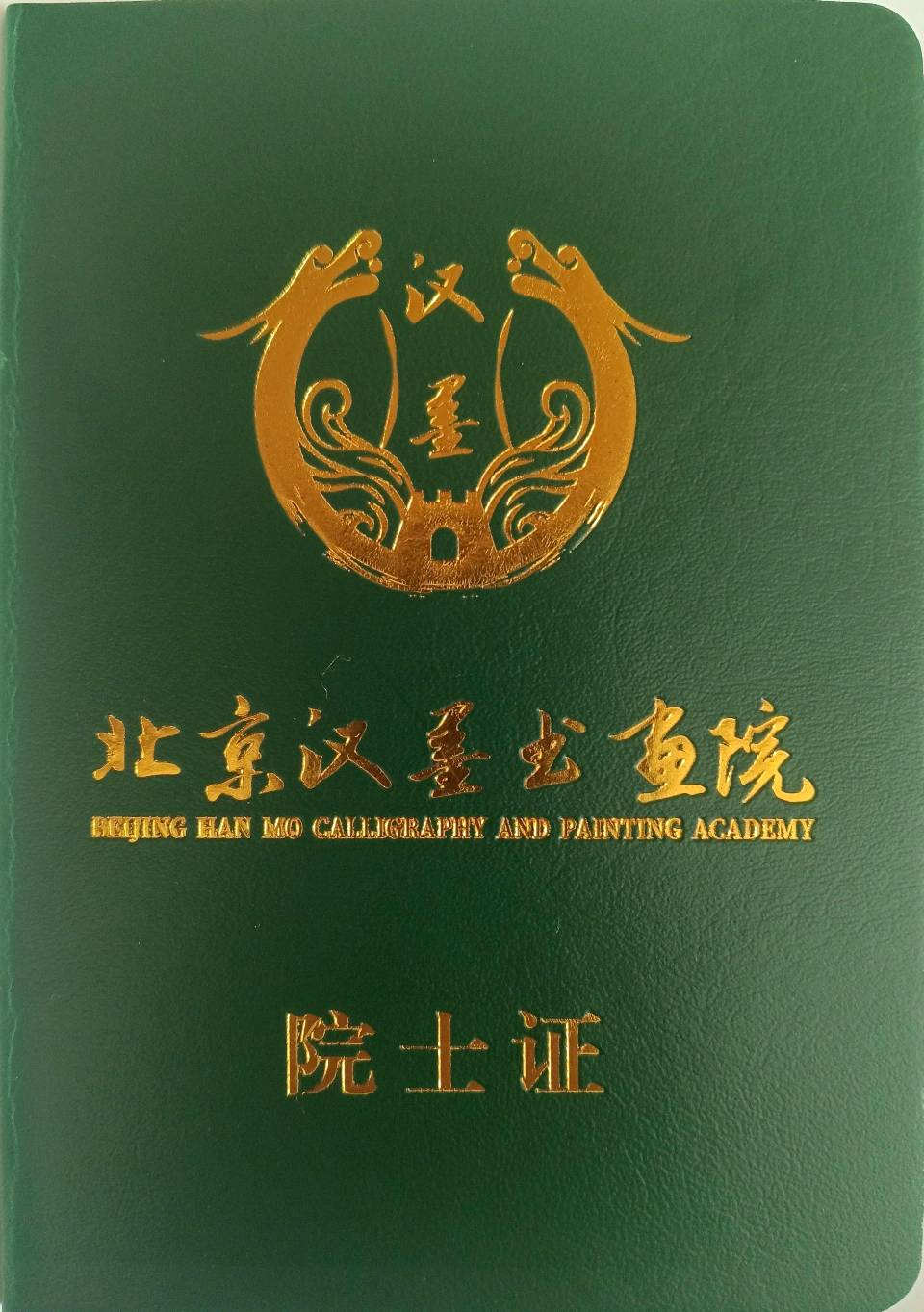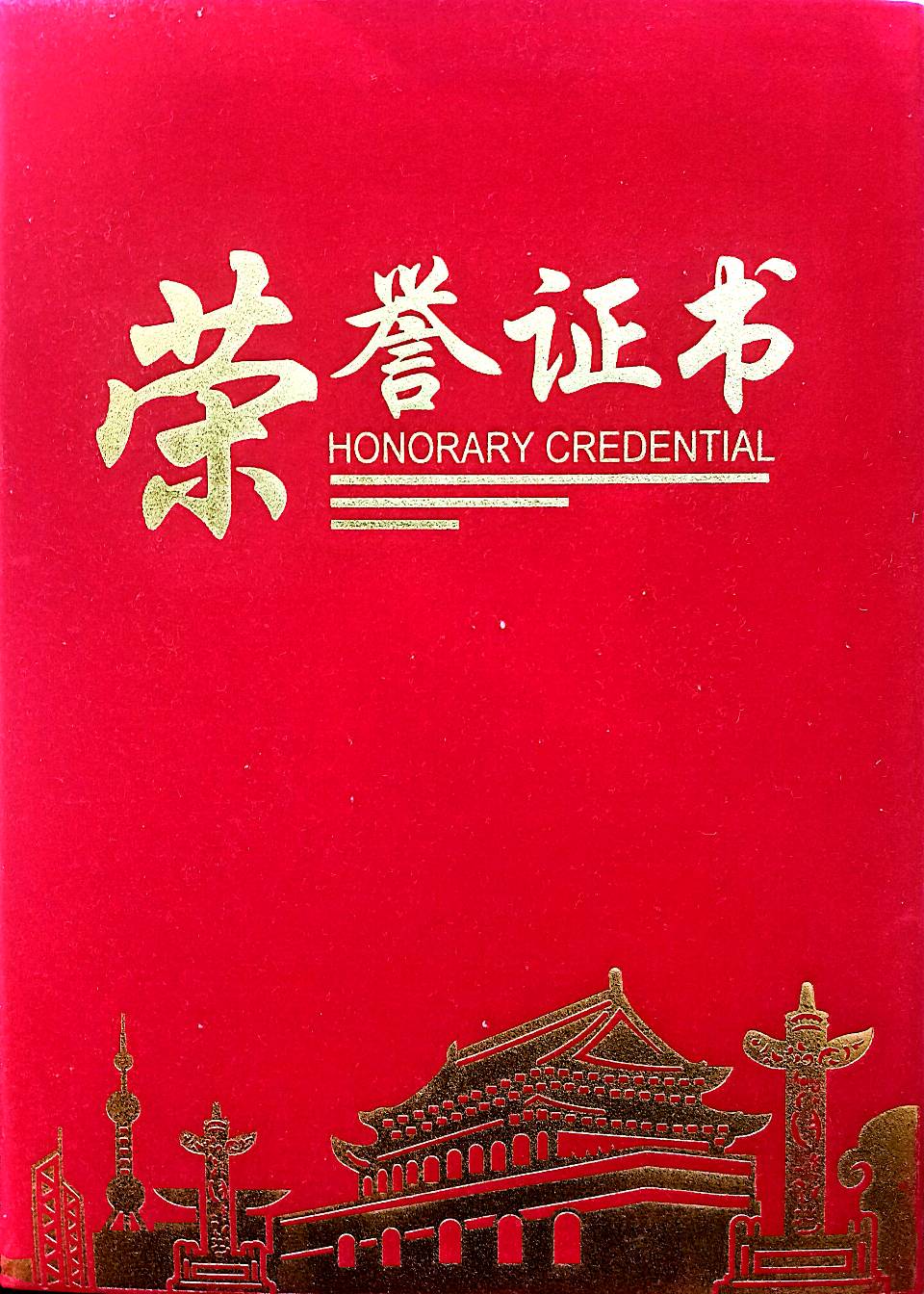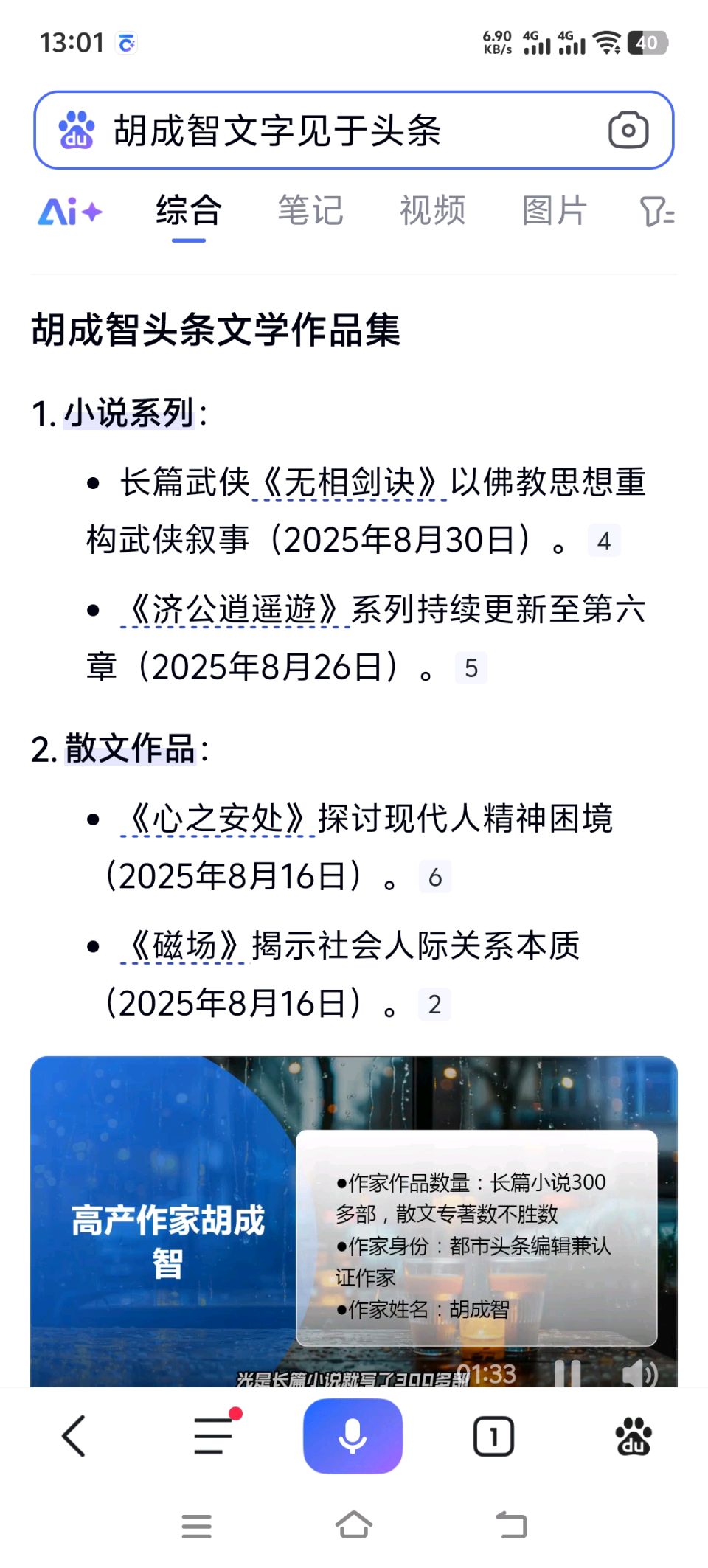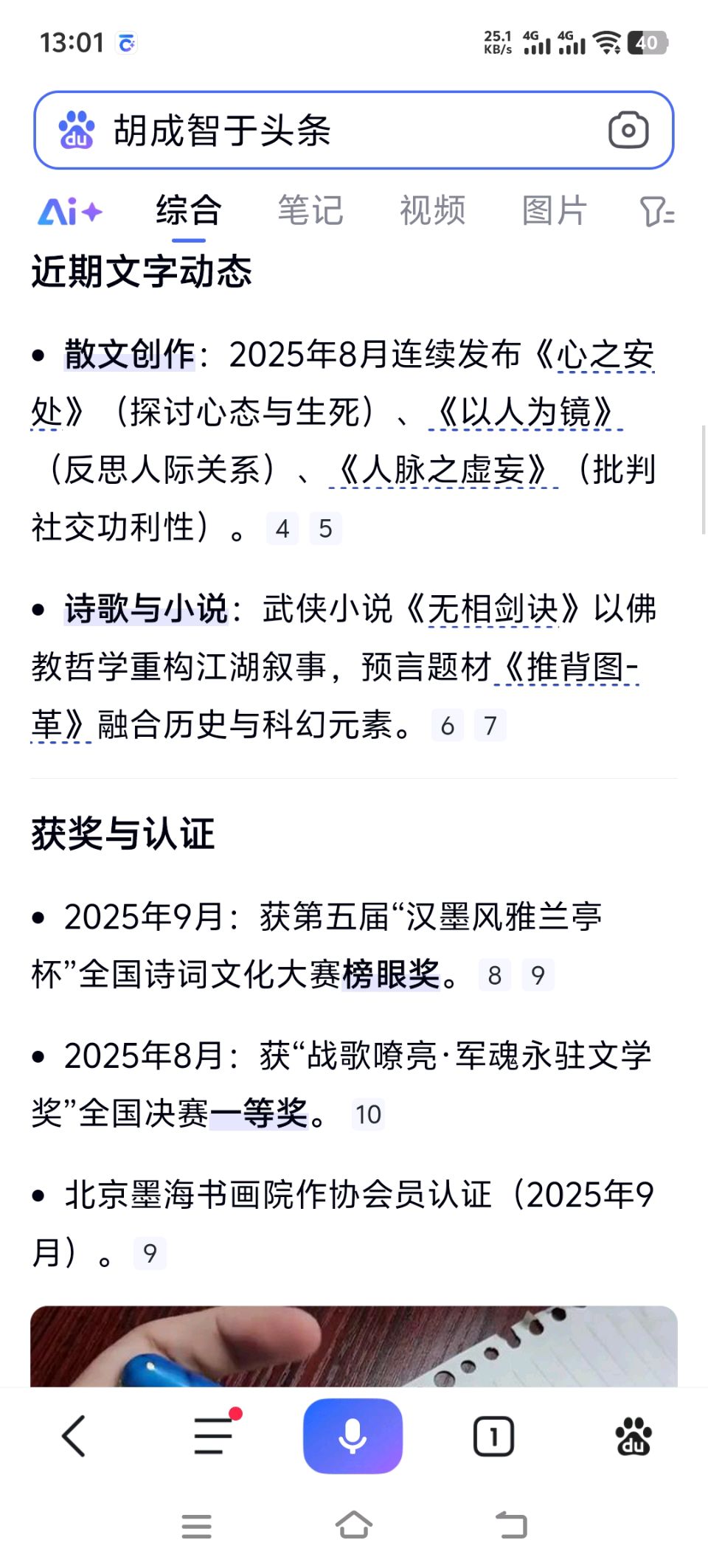---
《青春渡口》
第二卷 《离岸》
第五十七章 初雪無聲
省城的冬天,以一种不容置疑的、粗暴的方式宣告了它的来临。不再是秋日那种带着诗意的萧瑟,而是赤裸裸的、带着物理攻击性的严寒。北风如同被激怒的巨兽,日夜不停地咆哮着,从北方广袤的平原席卷而来,携带着细碎的、如同砂砾般的雪沫,抽打在行人的脸上、身上,生疼。天空总是阴沉着脸,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仿佛随时都会不堪重负,将更多的冰雪倾泻下来。
陋室的处境变得愈发艰难。那单薄的、糊了多层旧报纸也依旧漏风的墙壁,根本无法抵御这彻骨的寒意。屋内屋外,几乎成了同一个温度。呵气成霜,水缸里结了一层薄冰,每天早晨都需要用石头砸开才能取水。母亲周氏将家里所有能御寒的物件都搜罗了出来,破旧的棉被,打满补丁的棉衣,甚至一些不用的旧布,都层层叠叠地盖在身上、堵在门窗的缝隙里,但寒冷依旧如同无孔不入的水银,渗透进来,冻结着人的四肢,也冻结着本就稀薄的热气。
陈烬余的西药房夜班,成了名副其实的苦役。那间没有取暖设施的隔间,在冬夜里简直就是一个冰窖。他穿着所有能穿上的衣服,裹着母亲硬塞给他的一条破旧毛毯,依旧冻得浑身僵硬,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巡视店铺时,手脚都冻得麻木,几乎失去知觉,每一次推开隔间的门,都需要巨大的勇气。那盏昏暗的灯泡,在寒冷中似乎也变得愈发黯淡,投下的光影都带着一股冰冷的质感。他只能靠不停地踱步、用力搓揉双手、以及强打精神背诵那些需要记忆的知识点,来对抗那几乎要将人冻僵的睡意和寒冷。
学业上的压力,并未因天气的恶劣而有丝毫减轻。期末的临近,像另一座缓缓逼近的大山,投下越来越长的阴影。课程进度更快,内容更深,对综合能力的要求也更高。陈烬余感觉自己像是在泥泞的沼泽中跋涉,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力气,而身后,那些尚未完全掌握的知识点,如同沼泽中的淤泥,不断拖拽着他,让他举步维艰。
这天夜里,他在西药房的隔间,就着那盏冰冷的灯光,试图攻克一道复杂的物理习题。手指冻得有些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迹歪歪扭扭。思路也像是被冻住了一般,滞涩难通。他反复演算,却总是在某个环节卡住,不得其法。焦躁、寒冷、疲惫……种种负面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他逼到崩溃的边缘。
就在这时,他无意间抬起头,透过布满冰凌的、模糊的窗户玻璃,看向外面。
下雪了。
不是之前那种细碎的雪沫,而是真正的、鹅毛般的大雪。无声无息,却又铺天盖地。雪花在窗外昏黄路灯的光晕中,密集地、悠然地飘落,覆盖了街道、屋顶、以及远处模糊的建筑轮廓。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这漫天飞舞的、纯粹的白色。
陈烬余怔怔地看着。
这寂静的、浩大的雪,与他内心翻腾的焦躁和困境,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它不像梧城县的雪,带着江南的温润与诗意;省城的雪,是冰冷的,沉默的,带着一种北方特有的、近乎残酷的壮美。它不在乎人间的悲欢,不在乎一個窮學生的掙扎,只是按照自然的律令,冷漠地、持續地覆蓋著一切。
然而,奇怪的是,看著這無聲而落的大雪,陳燼余心中那團焦灼的火焰,竟慢慢地平息了下來。一種更深的、近乎虛無的平靜,取代了之前的煩躁。
他放下筆,走到窗邊,將臉貼在冰冷的玻璃上,感受著那刺骨的涼意透過皮膚傳來。
在這絕對的寒冷與寂靜中,他忽然覺得,自己的那點痛苦與掙扎,是多麼的渺小,多麼的微不足道。就像這漫天大雪中的一片雪花,無論它曾經如何翻飛掙扎,最終都將歸於這片白茫茫的、無聲的大地。
這並非絕望,而是一種奇異的釋然。
他不再強迫自己繼續演算那道難題。他只是靜靜地站在窗前,看著雪落,聽著(或者說感受著)那無邊的寂靜。
不知過了多久,直到手腳都凍得幾乎失去知覺,他才緩緩轉過身,重新坐回那張冰冷的行軍床。
初雪無聲,覆蓋了省城的喧囂,也暫時冷卻了他心頭的焦灼。
前路依然艱難,寒冷依舊刺骨。
但至少在此刻,在這片被大雪包裹的寂靜裡,他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冰冷的清醒。
第五十八章 沈先生的爐火
大雪断断续续下了两日,将省城彻底染成一片单调而刺眼的银白。气温骤降,呵气成冰,连平日里最喧嚣的街道也变得人迹罕至,只有清理积雪的工人和少数为了生计不得不奔波的人,在没过脚踝的雪地里,留下深深浅浅、很快又被新雪覆盖的脚印。
陈烬余从西药房下夜班回来,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快要被冻僵了。每一步都像是在冰冷的泥淖中挣扎,寒气透过单薄的鞋底和磨得发亮的裤管,直往骨头缝里钻。咳嗽变得愈发剧烈和频繁,每一次都像是要把肺叶从胸腔里撕扯出来,带来一阵阵尖锐的疼痛和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喘息。喉咙里仿佛堵着一团沾满冰碴的棉絮,又痒又痛。
回到陋室,那点可怜的温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母亲忧心忡忡地看着他冻得发紫的嘴唇和苍白的脸色,想给他熬碗姜汤,却发现连最后一块姜也已经在昨天用完了。父亲陈知书依旧沉默地坐在角落里,裹着那件破旧的棉袍,像一尊被冻结的雕像,只有偶尔看向儿子时,那微微蹙起的眉头,泄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天下午,陈烬余照例去了图书馆。与室外酷寒相比,图书馆里虽然也算不上温暖,但至少隔绝了那割人肌肤的寒风。他走到自己那个靠里的角落,习惯性地搓了搓冻得僵硬的手指,才从书包里拿出书本。
然而,今天的图书馆,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煤火气味?还夹杂着一丝极细微的、属于食物的温暖香气?
他疑惑地抬起头,循着气味望去。只见在柜台旁边,那个平日里空着的、靠近暖气管道(虽然那暖气也几乎只是象征性地有点温度)的角落里,不知何时,竟摆放了一个小小的、看起来颇为古旧的黄铜炭炉!
炭炉里,几块银炭正安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橘红色的、温暖的光晕,驱散了周遭一小片区域的寒意。炭炉上,还架着一个同样小巧的、冒着丝丝热气的陶罐,那温暖的香气,正是从陶罐里散发出来的。
而沈先生,就坐在炭炉旁边的一把旧藤椅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正就着炭炉温暖的光线,低头阅读着一本厚厚的、纸页泛黄的书。炉火的光映在他清癯的脸上,将那平日里显得有些严肃的线条,柔和了许多。
陈烬余愣住了。他从未在图书馆里见过如此……具有生活气息的景象。这炭炉,这陶罐,这毯子,与图书馆那庄严肃穆的氛围,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融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家的温暖感。
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沈先生从书页上抬起头,扶了扶金丝眼镜,看向他,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用他那惯常的、平和的语气说道:“外面雪大,这里暖和些。过来坐吧。”
陈烬余的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他迟疑了片刻,还是依言走了过去,在炭炉旁边另一张空着的、看起来同样有些年头的矮凳上,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
一股实实在在的、久违的暖意,瞬间包裹了他几乎冻僵的身体。炭火的热量透过衣物,温暖着他冰冷的皮肤,也仿佛一点点渗透进他几乎被冻住的血液里。那陶罐里散发出的、带着淡淡米粮香气的热气,更是让他空乏而冰冷的肠胃,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渴望的痉挛。
他局促地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有些不知所措。
沈先生没有看他,目光重新落回书页上,仿佛只是随口邀请了一位普通的读者过来取暖。但他那平静的姿态,却让陈烬余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
图书馆里依旧安静,只有炭火偶尔发出的细微噼啪声,陶罐里汤汁滚沸的咕嘟声,以及书页翻动的沙沙声。在这片由寒冷隔绝出来的、温暖而宁静的小小空间里,时间仿佛都放缓了脚步。
陈烬余偷偷抬起眼,看着跳动的炉火,看着沈先生那专注阅读的侧影,看着陶罐口袅袅升起的热气……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感激、温暖和一丝酸楚的情绪,在他心中弥漫开来。
他知道,这炭炉,这陶罐,绝非图书馆的常设。这或许是沈先生自己带来的,在这酷寒的冬日,为自己,也或许……是为他这个总是独自在角落里、与寒冷和困顿抗争的年轻读者,特意营造出的一小片绿洲。
没有言语,没有刻意的关怀。
只有这无声的炉火,这温暖的存在。
陈烬余默默地低下头,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书本和那支旧钢笔。他没有再感到之前的寒冷和僵硬,手指也灵活了许多。他就着这难得的温暖和光亮,开始专注地学习起来。
偶尔,沈先生会起身,用一块厚布垫着,将陶罐的盖子揭开,用一个小勺轻轻搅动一下里面的粥汤(陈烬余看清了,那是很普通的白米粥),然后又盖上。那动作自然而从容,仿佛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陈烬余没有道谢。他知道,有些感激,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他只是更加用力地握紧了手中的笔,将这份无声的温暖,化作笔尖下更加坚定的字迹。
窗外,大雪依旧无声地覆盖着省城。
但在这图书馆的角落里,一炉炭火,一碗热粥,一个沉默的长者,一个奋发的少年,共同构成了一幅抵御严寒的、充满人性温度的画卷。
这温暖,不足以融化整个冬天的冰雪,却足以照亮一颗在寒夜中前行的心。
第五十九章 父親的咳嗽聲
沈先生圖書館角落裡那盆無聲的爐火,像一顆被小心翼翼珍藏起來的火種,在陳燼余冰封的心田裡持續散發著餘溫,給予了他對抗省城嚴冬的、額外的勇氣與力量。然而,當他頂著風雪回到那間四處漏風的陋室時,現實的冰冷與殘酷,便再次以更加具體和令人憂慮的方式,撲面而來。
父親陳知書病倒了。
起初只是幾聲壓抑的、偶爾的咳嗽,在陳燼余夜歸或清晨離家時,從布簾後傳來。陳燼余並未太過在意,省城的冬天,咳嗽彷彿是大多數貧苦人的標配。但很快,那咳嗽聲變得頻繁、劇烈而持久起來。
那不再是簡單的清喉嚨,而是一種從胸腔深處爆發出來的、帶著撕裂感的、沉悶而艱澀的聲響。每一次發作,都像是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用力掏挖著他的肺葉,伴隨著劇烈的、彷彿要將五臟六腑都震移位了的喘息。咳嗽過後,往往是長時間的、令人窒息的寂靜,只能聽到他粗重而艱難的換氣聲,像一架破舊的、隨時都會散架的風箱。
陋室狹小,這驚心動魄的咳嗽聲無處不在,像一片濃重的陰影,籠罩著這個本就壓抑的空間。母親周氏的臉上,憂慮之色日益濃重。她翻箱倒櫃,找出一些不知從哪裡得來的、早已乾枯發黴的草藥根莖,熬成散發著古怪氣味的、黑乎乎的湯水,逼著父親喝下。但那湯水似乎並無效果,咳嗽依舊,甚至連帶著父親的臉色,也開始呈現出一種不健康的、灰敗的潮紅,顴骨處尤其明顯。
陳燼余夜裡從西藥房回來,常常能聽到父母壓低聲音的、斷斷續續的交談。
“……還是得去看看大夫……”母親的聲音帶著哭腔。
“看什麼大夫……咳咳……哪來的錢……死不了……”父親的聲音嘶啞、虛弱,卻依舊帶著那股熟悉的、固執的硬氣,只是那硬氣在病痛的折磨下,顯得有些外強中乾。
“可是……”
“沒有可是!熬一熬……開春就好了……咳咳咳……”
又是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打斷了對話。
陳燼余站在門外,聽著布簾後那壓抑的痛苦聲響,聽著母親那無助的啜泣,手腳一片冰涼。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父親拒絕就醫,不僅僅是因為錢。那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對自身尊嚴的維護,一種不願再給這個已經風雨飄搖的家庭增添任何負累的、近乎自虐般的堅持。
父親的咳嗽聲,成了這個冬天最令人揪心的背景音。它比省城的寒風更冷,比西藥房的長夜更漫長。它像一根無形的鞭子,抽打在陳燼余的心上,提醒著他這個家庭的脆弱,提醒著他肩上那尚未卸下的、沉重的責任。
他看著父親日漸佝僂的身影和那張因為病痛與隱忍而愈發顯得嚴峻的臉,心中充滿了一種複雜難言的情緒。有擔憂,有心痛,有愧疚,也有一絲……難以置信的、彷彿在共同承受苦難中悄然滋生出的、近乎平等的親近感。
他開始更加留意父親的狀況。每天出門前,會偷偷觀察父親的臉色;晚上回來,會側耳傾聽布簾後的動靜。他甚至利用在西藥房工作的便利,偷偷詢問過店裡那個總是板著臉的掌櫃,關於治療風寒咳嗽的、價格最便宜的西藥。掌櫃報出的那個數字,讓他剛剛升起的念頭,又瞬間沉了下去。
他所能做的,似乎只有更加拼命。他希望能用更好的成績,來換取或許存在的獎學金機會;他希望能在學業之外,找到更多賺錢的門路。每一次他在學業上取得一點微小的進步,每一次他將辛苦掙來的銅板交給母親時,他都隱隱期盼著,這或許能減輕父親心頭一點點壓力,或許能讓那該死的咳嗽聲,稍微緩和一些。
然而,現實是,父親的咳嗽聲,依舊在每一個寒冷的夜晚和清晨,固執地響起,如同這個家庭命運的、沉重而不祥的註腳。
它提醒著陳烬余,冬天的考驗,不僅僅是學業與生存,更是與親人的健康、與時間的賽跑。
這場賽跑,他輸不起。
第六十章 冬夜的微光
父親日漸沉重的咳嗽聲,像一片不斷增厚的陰雲,低低地壓在陋室的上空,也壓在陳燼余的心頭。它讓省城的這個冬天,變得格外漫長而難熬。每一聲壓抑的、從胸腔深處掙扎而出的悶響,都像是一記重錘,敲打著這個家庭本就脆弱的神經,也催促著陳燼余必須更快地成長,更堅韌地擔當。
生活的節奏愈發緊繃得像一根隨時會斷裂的弦。學業、西藥房的夜班、對父親病情的憂慮,以及那份始終沉甸甸的經濟壓力,交織成一張無形的、越收越緊的網。陳燼余感覺自己像一頭被蒙上眼睛、拴在磨盤上的騾子,只能憑藉著一股本能,在這看似無盡的循環中,麻木而機械地向前、向前。
然而,正是在這極致的壓抑與灰暗之中,一些極其微小的、幾乎難以察覺的變化,如同冬日凍土下悄然蠕動的種子,正在頑強地醞釀著生機。
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母親周氏身上。面對丈夫日益加重的病情和兒子的沉默拼搏,這個一向柔順甚至有些懦弱的婦人,骨子裡那份屬於母親的韌性與剛強,被徹底激發了出來。她不再動輒垂淚,也不再只是無助地嘆息。她的眼神裡,多了一種近乎狠厲的決絕。她更加瘋狂地接取各種零活,漿洗、縫補、甚至幫人拆卸那種極其傷手的漁網,雙手紅腫開裂得不成樣子,卻從未聽她抱怨過一句。她將每一分賺來的錢都仔細收好,計算著距離下一次繳納房租、購買糧食和……或許能為丈夫抓一副便宜草藥的數額。她成了這個家庭在絕境中,最堅實、最沉默的基石。
而父親陳知書,在病痛的折磨下,那層包裹著他的、堅硬的冰殼,似乎也出現了些許裂痕。他依舊沉默,依舊拒絕就醫,但對陳燼余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種極其微妙、幾乎難以察覺的轉變。
那是一個罕見的、沒有下雪的夜晚,但寒意依舊刺骨。陳燼余從西藥房回來,已是後半夜。他輕手輕腳地推開門,生怕驚擾了可能剛剛睡下的父母。
陋室裡一片漆黑,只有從布簾的縫隙裡,透出一絲極其微弱的、搖曳的光亮——那是母親為父親留的一盞小油燈。
他正準備摸黑走向自己的床鋪,布簾後,卻傳來了父親低沉而沙啞的聲音,因為壓抑著咳嗽,顯得有些斷續:
“回……回來了?”
陳燼余腳步一頓,低聲應道:“嗯,爹,我回來了。”
布簾後沉默了片刻,然後,父親的聲音再次響起,帶著一種陳燼余從未聽過的、近乎遲疑的語氣:
“外面……冷得緊吧?”
一句簡單的、關於天氣的問話。如此平常,如此普通。
但在此刻,在這個寒冷的冬夜,從一向惜字如金、威嚴冷硬的父親口中問出,卻像一道微弱的電流,瞬間擊中了陳燼余。他愣在原地,鼻子猛地一酸。
“還……還好。”他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
“嗯。”父親應了一聲,便不再說話。布簾後,傳來他壓抑的、艱難的翻身聲,和幾聲極力控制的、悶悶的咳嗽。
陳燼余站在原地,在濃稠的黑暗裡,靜靜地聽著。心中百感交集。
沒有溫情的擁抱,沒有感人肺腑的長談,甚至沒有對彼此處境的一句明確關切。
只有一句關於寒冷的詢問。
但這已經足夠了。
這句詢問,像一粒小小的火石,在父子之間那冰封已久的關係上,磕碰出了一星轉瞬即逝、卻真實存在的火花。它微弱,卻足以在這一刻,照亮彼此內心那深藏著的、從未熄滅的牽掛。
它意味著,父親看到了他的早出晚歸,感受到了他的辛苦。它意味著,那堵名為“父權”與“威嚴”的高牆,在共同的苦難與病痛的削弱下,終於裂開了一道縫隙,允許一絲屬於“人”的、最基本的溫情,艱難地流淌出來。
陳燼余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床邊,和衣躺下。身體依舊冰冷而疲憊,咳嗽的欲望也在喉嚨裡蠢蠢欲動。
但心中,卻因為那一句簡單的詢問,而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微弱卻真實的暖意。
這暖意,來自父親,來自母親那沉默的堅守,也來自他自己這幾個月來,不曾放棄的掙扎。
冬夜漫長,寒風呼嘯。
但在這間破敗的陋室裡,在無邊的黑暗與沉重中,確實有微光,在頑強地閃爍。
那是由苦難淬煉出的親情,是由絕境逼出的韌性,是一個寒門少年,在命運的洪流中,用他單薄的肩膀,為自己、也為家人,撐起的一小片、雖然殘破卻不容侵犯的天空。
這微光,不足以驅散整個冬天的嚴寒。
但它足以證明,生命,在任何境地下,都有其不可摧毀的尊嚴與力量。
【作者简介】胡成智,甘肃会宁县刘寨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汉墨书画院高级院士。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投身文学创作,现任都市头条编辑。《丛书》杂志社副主编。认证作家。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大专预科班学习,并于作家进修班深造。七律《咏寒门志士·三首》荣获第五届“汉墨风雅兰亭杯”全国诗词文化大赛榜眼奖。同时有二十多篇诗词获专家评审金奖,其军人题材诗词《郭养峰素怀》荣获全国第一届“战歌嘹亮-军魂永驻文学奖”一等奖;代表作《盲途疾行》荣获全国第十五届“墨海云帆杯”文学奖一等奖。中篇小说《金兰走西》在全国二十四家文艺单位联合举办的“春笋杯”文学评奖中获奖。
早期诗词作品多见于“歆竹苑文学网”,代表作包括《青山不碍白云飞》《故园赋》《影畔》《磁场》《江山咏怀十首》《尘寰感怀十四韵》《浮生不词》《群居赋》《觉醒之光》《诚实之罪》《盲途疾行》《文明孤途赋》等。近年来,先后出版《胡成智文集》【诗词篇】【小说篇】三部曲及《胡成智文集【地理篇】》三部曲。其长篇小说创作涵盖《山狐泪》《独魂记》《麦田里的沉默》《尘缘债海录》《闭聪录》《三界因果录》《般若红尘录》《佛心石》《松树沟的教书人》《向阳而生》《静水深流》《尘缘未央》《风水宝鉴》《逆行者》《黄土深处的回响》《经纬沧桑》《青蝉志异》《荒冢野史》《青峦血》《乡土之上》《素心笺》《逆流而上》《残霜刃》《山医》《翠峦烟雨录》《血秧》《地脉藏龙》《北辰星墟录》《九星龙脉诀》《三合缘》《无相剑诀》《青峰狐缘》《云台山寺传奇》《青娥听法录》《九渊重光录》《明光剑影录》《与自己的休战书》《看开的快乐》《青山锋芒》《无处安放的青春》《归园蜜语》《听雨居》《山中人》《山与海的对话》《乡村的饭香》《稻草》《轻描淡写》《香魂蝶魄录》《云岭茶香》《山岚深处的约定》《青山依旧锁情深》《青山遮不住》《云雾深处的誓言》《山茶谣》《青山几万重》《溪山烟雨录》《黄土魂》《锈钉记》《荒山泪》《残影碑》《沧海横流》《山鬼》《千秋山河鉴》《无锋之怒》《天命箴言录》《破相思》《碧落红尘》《无待神帝》《明月孤刀》《灵台照影录》《荒原之恋》《雾隐相思佩》《孤灯断剑录》《龙脉诡谭》《云梦相思骨》《山河龙隐录》《乾坤返气录》《痣命天机》《千峰辞》《幽冥山缘录》《明月孤鸿》《龙渊剑影》《荒岭残灯录》《天衍道行》《灵渊觉行》《悟光神域》《天命裁缝铺》《剑匣里的心跳》《玉碎京华》《九转星穹诀》《心相山海》《星陨幽冥录》《九霄龙吟传》《天咒秘玄录》《璇玑血》《玉阙恩仇录》《一句顶半生》系列二十六部,以及《济公逍遥遊》系列三十部。长篇小说总创作量达三百余部,作品总数一万余篇,目前大部分仍在整理陆续发表中。
自八十年代后期,又长期致力于周易八卦的预测应用,并深入钻研地理风水的理论与实践。近三十年来,撰有《山地风水辨疏》《平洋要旨》《六十透地龙分金秘旨》等六部地理专著,均收录于《胡成智文集【地理篇】》。该文集属内部资料,未完全公开,部分地理著述正逐步于网络平台发布。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