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杨延斌推荐语:25年前,我亦师亦友的北大荒作家杨孟勇,创造了57岁做心脏移植的世界奇迹,并接续创造了心脏移植不久后停止服药、健康地存活了25年的人间神话。杨孟勇用一颗不正常的心脏,把生命的不可能活成了可能!他的神奇故事,曾经由中央电视台等几十家电视台制作专题广为传播。长篇纪实散文《活下来再说》,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推荐连载此书,意在引起读者对生命的尊重和感动,同时感受这个社会的优越和温暖。尤其要向给予杨孟勇二次生命的哈医大二院、及其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著/杨孟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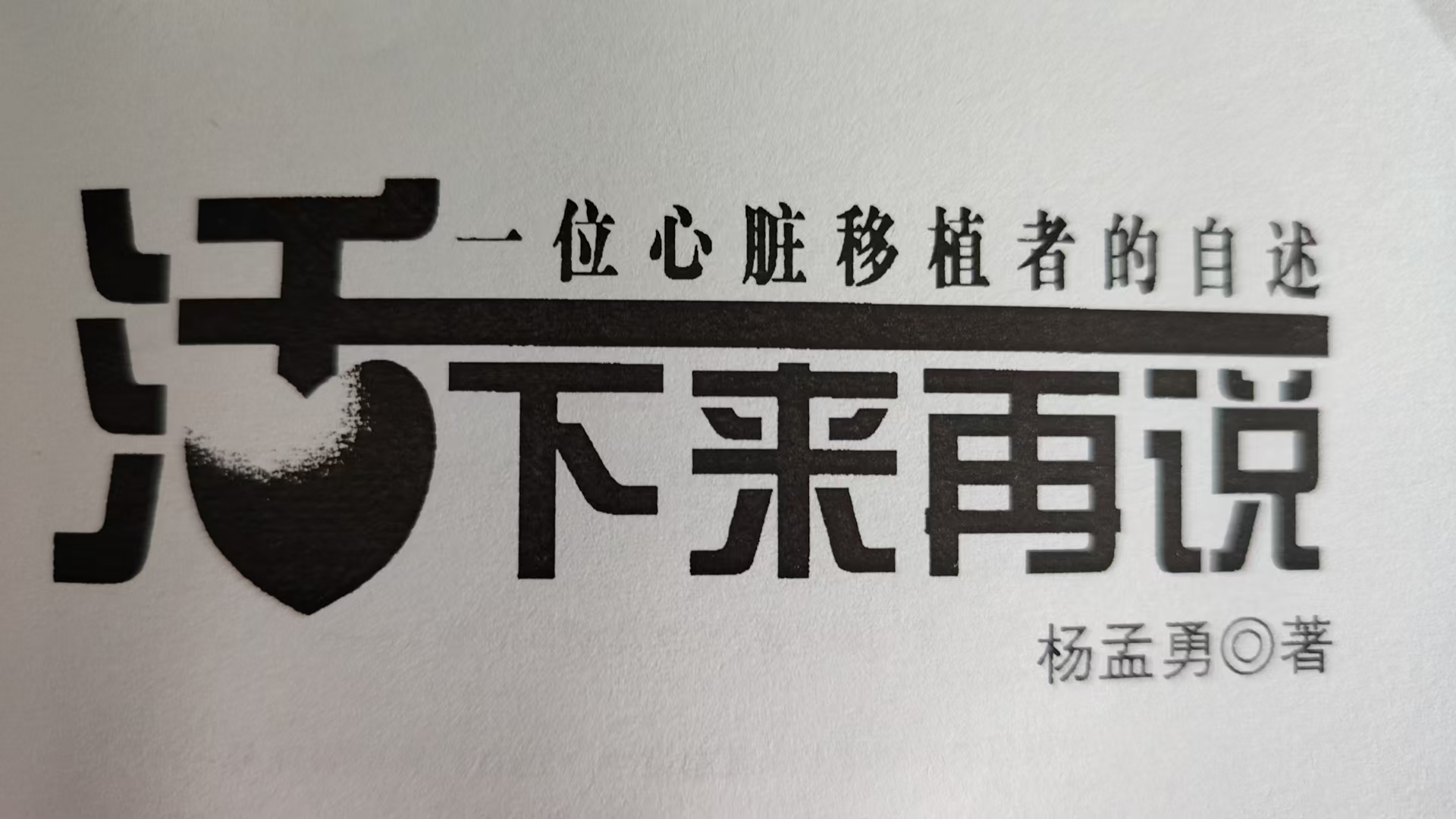
54、换心之后为什么闻到鱼腥就恶心
在此之前,说我对心脏移植的概念丝毫不知,怕是一种疏忽和遗漏。认真想来,许多年前曾经听到有人讲过,说的是一个同我一样的心脏移植者,发觉了自己的饮食口味儿有了很大改变,为了验证他的口味儿改变是否与心脏供体有关,便一路寻了去。中间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了供体的一些线索。曾经生活在供体身边的人证实,他的饮食口味儿确实与受体现在的口味儿相同。
这是部外国小说。听了讲述之后,只觉得新奇与神秘。今后遇上了,买一本来看。怎奈书海无涯,直到做了病人,也没有发现哪里的书店有卖,或是哪个朋友家中存有。
现在不必了。即使那本书印出来,或朋友来了电话,说他家正巧珍藏了一本,我也不会为此产生一阵欣喜的。原因是我觉得此时的我,与那篇小说中的人物相似,同样发现了自己的口味儿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57岁之前,嗜鱼如命的我,突然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变成了吃鱼就会发生呕吐的人。
闽江小区的马路对面,是闽江菜市场。那里一年四季有时鲜水果蔬菜供应,每天早晨,妻都要去市场一趟,买回一天的所需。
我逐渐恢复的时候,夏求明教授专程到病房对我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作了一次指导。
他说:“你今后要戒烟戒酒。”
我告诉他:“我是滴酒不沾的。烟也不吸一口,酒精过敏,尼古丁也同样过敏。”
夏教授满意地说:“这太好啦。”
问他:“还要注意什么?”
他说:“饮食一定要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尤其肥肉。”
“这正合我意,我一小就不吃肉,过年从不吃肉饺子。"我说。妻在一旁问:“夏教授,他今后可以吃点鱼吗?”
夏教授点点头说:“可以。鱼肉里蛋白质多,可以吃。还可以喝些茶。”
这个清淡的食谱很合我的胃口,尤其是鱼类。
我打小生活在胶东半岛靠海较近的小山村。村里每5天一个集市,光是贩卖鱼虾的鱼市就能排出二里长。父亲没死之前,把地里的活计匆匆做完,就推上小独轮车,一路山道去了烟台。卖掉了一车劈柴,买些鱼虾回来,蹲在集市上叫卖。卖不了的,自然就做了全家的菜肴了。我打小是吃鱼虾长大的,记得不赶集的时候,外村的小贩子就把螃蟹煮得红红的,用扁担挑上,沿村叫卖。一旦听到叫卖声远远地传过来,我立即奔向后院的几棵香椿树,偷偷掐下一抱嫩芽,跑到小贩那里去换一只美味螃蟹,躲在一旁偷偷地吃。
妻深知我一小形成的口味儿,每天按夏教授的饮食方案选购蔬菜。
那天她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进屋就喊:“孟勇--你来看呀,我给你买回什么来了?-你最愿意吃的呀!”
原来妻买回一块鱼。“这些天上顿茄子,下顿西红柿,也该给你改善一下了。”她说。
“那是什么鱼?”我提醒她,“不是上次的鲫鱼吧?上次怎么搞的,本来是很鲜的鲫鱼,吃起来味儿就变了。”
妻说:“这次可不是鲫鱼,你猜猜看。这种鱼你从前吃过,一定能记得。”
“看样子那条鱼很大。"我试探着问。
“什么鱼有六七十斤重呢?卖鱼的人把它砍成小块,我买的这块3斤多。”妻说。
鱼虽大,鳞片却很细小,我忽然想起来了,那就是黑龙江水系有名的三花五罗儿之一的哲罗鱼。在冰雪覆盖的梧桐河上,我还用鱼叉叉过呢。
“对啦-”妻说,“卖鱼的人一个劲儿地叫喊,哲罗啦,哲罗啦,有名的三花五罗儿啦。我上前一看,果然和你那年叉的那条一模一样,大脑袋,大嘴,身子圆咕隆咚的。我就买下这一块,现在开始馋了吧?”
我说:“这种鱼可是越来越少了,今天让你碰上了,赶快做鱼吧,这鱼的味道一定鲜美!”
那天中午,与多年前我叉到哲罗鱼那天的饭菜一模一样,雪白的米饭,红焖鱼块。这样的饭菜,本该美美地吃一顿,可是吃下第一口鱼,我就把碗筷一放,皱起眉头问妻:“这鱼怎么做的?放醋了吗?”
“红焖鱼,能不放醋吗?"妻看到我一副不满意的样子,解释说。
“开锅后用酒喷了吗?"我又问。
妻说:“喷了呀,怎么啦?”
我有些不满意:“腥,这鱼太腥!"
海光只顾低头吃,看我放下饭碗,有些奇怪地说:“我吃挺香,一点儿也不腥气呀。”
“要不就不是哲罗。"我用一根筷子蘸了蘸鱼汤,在舌头上舔了舔,再一次品了一下鱼汤的味道说,“哲罗哪能这么腥?"
"刚才你不是看了吗?”妻端着碗:“你说那细细的鳞片和鳞片上的花纹,与那年你叉的那条哲罗不是一模一样吗?连身子的形状都不差分毫。再说,那年你叉回鱼,我也是用这种方法红焖的呀,那年的就香得不得了,今天就腥得一口吃不下?”
妻放下碗,扭身走到里屋。她有些生气了。
海光随即跟到屋里去劝说:“妈--我爸嫌腥,就给他另做个菜吧,他现在变了,真的变啦,从前整天钓鱼叉鱼,天天吃鱼也不嫌腥,今天这么好的名贵鱼竟嫌腥了。妈爸不吃我吃--”儿子在安慰母亲。
我呆坐着,把海光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是的,我现在怎么竟不能吃鱼了呢?我试探着用筷子夹起一块鱼肉,放进嘴里,想再一次验证一下,我是否真的就有了什么变化。果然一股腥气漫上来,引起胃部一阵抽搐,我忍受不了,哇的一声向外吐了一口。我在心里认定,真的不能吃鱼了。上次的鲫鱼并不是死鱼,也没腐烂,妻买回来还活蹦乱跳,用装了水的方便袋提回来的。这样鲜活的鱼熬汤,我只喝了几口就不想再喝。今天的哲罗又引起我的呕吐。孩子的话,或许有些道理。
做了心脏移植的我,变化十分明显。
55、雪中的乐趣
这些年,北方大打冰雪牌,经济这两个字已经变为一个奇怪的杠杆,把严寒和低温给撬动了。官方公布的数字说,一年下来,竟有75万人参加了冰雪旅游。往日无用的甚至冻伤人冻死人的积雪和冰块,如今变成滚滚财源,也为黑龙江省增添了一抹亮色。
眼下,滑雪是北方人的时尚,在黑龙江多年,未曾滑过雪,也没有见过雪杖和滑雪板,只是在《林海雪原》的小说里看见杨子荣和剿匪小分队在林海雪原中飞驰。换了心脏之后,却有了一次百年不遇的机会。那次滑雪不是外地游客纷纷涌进黑龙江的高峰期,却是二月初,若是南方,早已花红柳绿,北方依然冰雪相伴。
早饭后,妻照例收拾好屋子,自己到外面散步去了,我接到了崔琳教授的电话,问我住在哪个区哪条街上,以及门牌号码等,说他坐的车已走在半路上,要来接我。
考虑到不好找,我们约定好了会面地点,放下电话,拎上个小兜向约定地点走去,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去滑雪。
车进蓝天雪场,已是中午,推开车门,一脚迈下来,踩在雪地上,只感到脚下软绵绵的。滑雪场迎接我的工作人员说,现在雪的颗粒正在变小变细,这才是滑雪的最佳时节。我看了一眼不远的山坡上,几个矫健的身影正从雪道上飞一样冲来,那情景令人数动,令人跃跃欲试。
进了准备大厅,每人领取一副雪板、雪杖和一双特制的硬壳靴,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我把双脚伸进硬壳靴里,雪板固定在靴底上,很牢固。穿上雪板,扛上雪杖,欣喜若狂地从准备大厅的后门,向山坡上走去。穿上滑雪板走路,可不是闹着玩的,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鸭子般一步步走向雪的边缘。
这是医院自己的滑雪场,不比闻名遐迩的亚布力。看上去,山不高,坡度十分理想,白雪铺盖的山体出现了优美曲线,离开雪道的地方是依旧苍翠的松树林,这景色是在城里难以目睹的。对一个打了 8年猎的人,不啻是一次旧梦重温。不能不想起当年扛上狼牌双简枪,在天地一片洁白的雪地里行走的情景。好汉不提当年勇。还是雪场上见吧。但心里一直打鼓。滑雪可是第一次。
要想学会滑雪,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不用说从山顶上快速冲下来,就算原地不动,或者试探着滑动一点点,脚下一滑,身子一晃,也是要摔跤的。无奈,我那几张在滑雪场的留影,就是弯下腰,腋下挟了个雪杖摆个姿态出来而已,那是蒙人的。你想当一个杨子荣那样剿匪小分队的战士,起码要过好滑雪这一关。
可想而知的是,我这个60多岁的人在那天一共摔了多少跤,滚了多少个雪球。好在每次都是教练员们迅速赶到,把我拉起来,我也有把他们拽倒的时候,两个人扑倒在雪地上哈哈笑起来。这便是人在冰雪中最大的乐趣。
我爱雪,从小在北方长大的人没有一个不爱雪的。
北方第一场大雪往往在11月上旬,那时节,泥土已经封冻,冻层达30 多公分厚,这时准有一场雪。赶上特殊年份,国庆节就是一场,记得有一年下得没膝深,屈指算一下,只不过是中秋节的第二天。如古人所云:胡天八月即飞雪了。
在闽江小区度过了炎热的夏季,短暂的秋季,迎来第一场冬季的初雪。冷了几天后,天气突然变暖,暖得令人心醉,暖得令人如寒号鸟一样有了几分侥幸。灰色云层均匀布满天空,一丝风也没有,往日喧闹的小区,现在无声无息,静如一片无语的森林,其至有几分神秘。
这时,就要下雪了。像江南的雨那样,温温柔柔地下它一场。通常这样的雪是没有一定的,时大,时小。小的只扬扬洒洒飘了一阵子、就收场,大的能下它整整一天。那时的地面,山林,草原,都被第一场雪覆盖,太阳出来,天地一片刺眼的洁白。
真正的暴雪倒是赶上了一场。三叔把我领到北大荒的第四年,已经三月中旬,往年该是播种大麦的季节,天却阴沉得吓人,结果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雪。早晨6点,屋子里依旧漆黑一片,原来雪堆的高度超过窗户,整个房间被雪堆埋了起来。起早的人家推不开门,把气窗玻璃打碎,掏个洞爬了出去。哇--世界掉进雪海里去了!小村庄只能露出黑屋脊,矮一些的树,见不到树干,电线杆子矮了半截,成群的野鸡飞到草房的屋脊上寻找草籽,狍子陷在雪里活活被捉。那一年我有幸见到鄂伦春人骑马下了山,在我居住的小村庄前开枪打猎。一色的皮大衣皮帽子,你分不出男女猎手。
这就是塞北雪。
手术之后我曾经有过一丝忧虑,移植在我胸中的那颗心脏,不知这个冬季会怎么样?前些年每年冬季来临,总会生出一些惧怕感,怕严寒,怕漫长的冬季,几度产生了回胶东半岛的小山村躲上一冬的想法,今年还会惧怕冰雪吗?
第一场雪过去了,感觉相当好,往后也会不错的。很多疑虑一扫而光。这个冬天总有一股热流贴在身子上,走进风雪,走进严寒,有如青年时代那样有火力。
这个冬天,我不必再怀疑自己了。下雪的时候,甚至想跑下楼,像小时那样,伏卧在一场新雪之上,两眼一动不动长久地注视着远处比雪光还要明亮的地方。那是晨曦,那是瞬间透射而来的期望。红日喷薄而出了。雪原金光万道。
于是全身心的激情,在那一刻被点燃、被陶醉,与后来渐渐发生的疲劳和温馨轻抚心头相比,那一刻好像自己就是这洁白世界中的一片雪了,一片从天空中飘飘而落的雪。
现在的水上花园到处都是雪,夏日里的喷泉被冰封了,深沉优雅的《梁祝》在雪天是听不到的,美人蕉干枯的叶子上压了一层雪,白玉维纳斯与小天使们都沐浴在塞北的雪中。
南方人可以喝一场优美的下午茶,让好的心境降临。北方人可以伸手接住几朵大如波斯菊的雪花,让它在你的手心里渐渐还原为水,那水的清凉照样会随着经脉传遍周身的。
北方的孩子大都有这样的奇想:倘若纷纷而下的不是雪,是白糖或白面多好。是白糖,世界就更加甜美了;是白面,世界就更为富庶了。这奇想,不仅来自孩子,当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之后,大人们也产生过如此不着边际的幻想。
塞北的雪从何时起变得不柔情了,甚至有些不讲情面了呢?其实,那都是风在作祟,尤其是来自西伯利亚的肆无忌惮的狂风,一旦掀起,就成了人们所畏惧的暴风雪了,北方人叫它“大烟儿炮”。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琢磨这句土语。大字可以作通常的理解,烟字,也不甚费力,无非是大风把雪粉吹了起来,烟雾般弥漫了天空之意。惟独这炮字,如果有机会,你在大风暴中走上一遭,仔细听听那暴风狂怒,扫打雪地抽打树林和房屋所发出的,并不是啸叫,而是一阵阵如雷贯耳般轰隆隆的声响,你就理解了这一炮字的准确了。
但这绝不是雪的过错。
塞北,不可以没有雪。整个冬季与初春,你都可以看到银灰天空大幕上漫不经心地下着翩翩飞舞的雪花,如亿万只白蝴蝶耐不了天庭的孤寂,一起背叛,投奔了这广袤的塞北大地。
那时的雪是不化的,大地清冷又纯洁。恋人们双双对对在雪天里散步,赏雪,那也是我自己所亲历的情景。在一首诗中,我曾把这塞北称之为惟一用零度歌唱纯洁的地方,后来朋友写给我的一篇诗评的题目就叫《零度歌唱》。与雨的泥泞、淫雨的无尽相比,雪自然要高贵许多,它同一首诗一样,整个冬季都不在停地影响着我。
56、尴尬的洗浴液
正应了乐极生悲那句话,从滑雪场回来,就从快乐情绪的峰巅一下子跌入深谷。深谷中的我,不是生了什么悲愁,倒是身处一种无法说得明白,又无法脱得了的尴尬境地。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乘坐来时的丰田面包车返回市里,一进屋妻失声地叫起来,“我的天,你昨天去哪儿啦?我到处打电话,也找不到你的人影?”
我把小提兜往地上一放,说:“去滑雪场了!”
妻还蒙在鼓里:“什么滑雪场?”
“二院来车把我们几个拉到帽儿山蓝天滑雪场滑雪去啦!"我解释说。
妻埋怨我:“到了滑雪场也不来个电话,叫我担心了一夜。”接着又风趣地说:“你可是国宝啦,丢了可怎么交待。”
我说:“滑雪场不通电话,崔教授几次给你打手机都没信号,把我也急得够呛!”
妻又说:“那你走也该留个纸条在桌上,好让我放心哪。”
"说来也怪了,崔教授来电话时,正好你出去买菜,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去山区滑雪,上了车走出很远才知道。”
妻终于不说什么了,忙着整理床铺,她说:“坐车坐累了吧,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我躺下来,感到疲惫困乏一齐袭来,不久就昏然人睡,醒来已近中午,见妻手拿几个小巧的塑料瓶,那东西比拇指略粗,长约两寸,灰白色的,上面印了几个小小的字。妻问我:“这是什么?”
我没立即回答,原因是那一刻心中产生了无缘无故的羞愧感。
每次我从外面回来,妻都要细细检查我带回的物品,像海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那样严肃认真。这几乎都成为惯例了。
“这是兜里带回来的,是什么?”妻不去看小瓶上的文字,偏要问我。
我知道妻的用意了。不得不走过去,接过那几个小瓶看了看,硬着头皮说:“这不是洗浴液吗?”
妻继续追问:“是不是人家宾馆的?”
我被问懵了。怎么会呢?那天晚上我没洗澡,却带回了洗浴液。
问题很简单,妻怀疑我偷拿了滑雪场宾馆的。她脸色冷了下来,一声不响,找了个方便袋,非常严肃地把几瓶洗浴液装进去,准备扔掉。我急忙说:“别。”一把抢了过来,掖在卫生间旮旯里。像一个犯下过错的人在掩饰其行为。
现在仔细回想一下昨天的事,是很有必要的。
四小瓶洗浴液,有两瓶应该是同一房间老赵的,难道他没有用?就那么在热水里泡了泡?于是我就全部拿了回来?偷偷地拿了?
我开始飞快地检点自己,有必要弄清这几十年来,有无偷拿别人东西的历史。
我努力地回想,只记起小学一年级时产生过偷同学一支铅笔的念头,趁教室的人极少,把整个身子靠在了那个挂在墙上的书包上。表面很镇静,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把手背过去,偷偷伸进人家的书包里。我已经摸到了那支铅笔,抓在手里好久,却不敢拿出来,因为眼前总是有人见动,还有儿只眼睛不时地扫过明亮的目光。最后那支铅笔在我的手心里都攥热乎了,还是没敢把它拿出来。
这种明目张胆的偷的欲望,似乎只在儿时发生了这一次。事隔几十年,这种欲望能够死灰复燃?有些奇怪,又令人不解,在我去拿洗浴液的那一瞬间,为何没产生我小时偷人铅笔时的那种紧张和恐惧呢?直到妻发现了赃物,并一再追问,才慢慢以推理的方法得出自己偷拿了东西的结论。
下手干那件不光彩事情的时候,是我的自身,还是另外的人?遗憾的是,至今对我的供体知之甚少,莫非他曾经犯下过盗窃罪,是一个江洋大盗式的人物?
这是个悬案。
本不想提及这件事的,你不提,它也发生了。掩耳盗铃的故事谁都知道。
这个悬案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它让我时常懊悔,时常慌恐,也时常谴责自己,一个60多岁的人,为何堕落到如此地步。想不清楚的时候,会把供体这一事实拿出来分析一下。直到有一天,一个记者写一篇报道登在电视报上。报道上说:国外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一个小偷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位大学教授,后来发现那位教授也喑暗地开始了小偷小摸的行为。
这一次让我真正地紧张起来,总是愣怔在那里,一动不动,头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夜晚住在滑雪场宾馆的情景。
我甚至想打电话,问一问那晚同住一屋的老赵,是不是他洗完澡之后,没用洗浴液,就把他的那份和我的那份一起塞进了我的提兜里?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因为那天滑雪跌了不少的跟斗,左手小指摔出一道伤口,流了不少的血。因为流了血,因为怕伤口感染,我才没进洗澡间洗澡。
既然我没进洗澡间,没有放水洗澡,那四瓶洗浴液又怎么是我拿的呢?
不是我拿的,为何又出现在我的提兜里被妻翻了出来?
这件事一下子把我弄昏了头。那几天里总是打不起精神,像一个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的病人,两耳先是轰隆作响,而后则出现持续很久的尖锐的鸣叫声。整天恍恍惚惚的。
不行!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
我想让老赵帮我洗刷一下,至少他能给我打个证言什么的。他洗澡时,我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滑雪场有专门的接收天线,我看的是香港凤凰卫视。
老赵,挺憨厚的,老实巴交的一个人。相信他会作这个证明的。
后来一想,电话打过去,证明写好了,给我寄过来,又能怎样?
57、梦中逃亡的人是我吗
时常会有一些惶惶不安的感觉在心底渐渐滋生。这让我奇怪,又有些疑虑。那不安的念头十分清晰与强烈,不是你不去理会,它就会慢慢消失或自动减退的。
那种惶惶不安,很像一个正在被追捕中的人才会产生的。其中包含着一些恐惧。
出院之后的我,生活稳定,手术前的57年,没有触犯过法律,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相反地却屡屡遭受挫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这样的一种人,又不是眼下的高官,贪污受贿了千万资财,怎么会产生惶惶不可终日,总在担心会有什么人前来抓捕的感觉呢?
从另一个方面讲,诚实这两个字在我以往的生命中,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找出几件事情作证。上小学时,我曾在一个夜晚捡到一个钱包。当时的我,不敢私自留下,也不敢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打开。便忐忑不安地在黑夜里寻找到一间有灯光的办公室,敲门进去,把钱包交到一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手中。工作人员当着我的面,打开钱包数了数,整整63万元(1954年的旧币,等于新币63元)。
那时我还小。正由于小,才可以看清一个人最基本的构成是什么。俗语“三岁看老",还是有一番道理的。
可以说,以往的57岁,我是心安理得的。是没有负债感,也没有负罪感的一个人。今日缘何惶惶不安?
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种不安的感觉来临时,真的就像通缉令中在逃的犯人一般。
我突然明白了。那不是我。
惶惶不安的,应该是我的供体,应该是我胸腔中的那颗心脏。当年他一定惹下了杀身之祸,犯了弥天大罪,为躲避惩处,开始了逃亡。那些感觉至今还留在他心脏的每个细胞中。
那些惶恐不安的细胞,一定是与我的大脑取得了联系,经常在干扰我正常的生活。
我常在梦中被他取代,迫不得已同他一起走上了一条逃亡路。
一切像回到千万年以前的混沌。前面没有路,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荒古的衰草丛中穿越而过,那就是我。
夜晚无法辨别方向,无数草茎相互磨擦发出了窸窣声,我仍然没有逃出很远。
在这样的夜晚,快速奔逃在荒草丛中,出现刮风般的呼啸声,那是我奔逃的速度引起的。
我一直担心这清晰的声响,会在夜里传出很远。
我抱怨这长长的夜晚为什么如此不可靠,为什么就不能将我逃奔的声响掩盖一些,比如一场大风让野草像海浪似的涌动,带起洪水般的哗哗声。那时树梢也会在狂风中啸叫,我那跑动的身影和声音才能在风高草涌的暗夜被淹没。被淹没得越彻底越好。
他们的行动早已开始了,不把我捉拿到手不会罢休。
现在只要稍微放慢速度就会落人埋伏。
为了加快速度摆脱追捕,我试着用各种姿势奔逃。甚至弯下腰身,让两只前臂着地,后腿用力地一蹬地面,协调一致让身体向前跳跃,并保持惯性力。
这种新的奔跑方式显然加快了速度,遇到不宽的沟壑,可以一纵而过。对那些宽一点的河,只要发现得早,在快速的惯性中运足力气,四肢一起腾跳,就可轻盈地落在对岸,不至于扑通一下摔倒。
十分有效地奔逃了一段路程之后,我慢慢停下来,证实这种方法确实可以摆脱追踪,但我并没有放松半点警惕,更不能沾沾自喜。
前面似乎有个洞穴,穴口在一个土丘的侧面。天空已出现微光。这时我有些疲乏,很想在这个洞穴里休息一下,但必须在这个洞口周围观察有没有异常,当我蜷缩起身子即将往那个舒适的土洞里钻进去,会不会突然间从里面蹿出个什么。
我不能停留,后面追捕的人会越来越多,浩浩荡荡,虽然我加快了速度奔跑,但他们就在我后面不远的距离紧追不舍。
我必须快速奔跑,这一片荒原的下面,让我感到了奇异与松软,我担心腾跳起来的身子下落时会陷进去,或者误入一片泥沼不能自拔。那样用不多久,后面的追捕者就会赶到,抓住我双肩把我拖出来。
我不能在这样的荒野中停下脚步,担心一旦停下来,脚下就是一个为我挖好的陷阱,上面很可能用乱草或树枝加以伪装,下面是很窄的窖,任何动物的腿脚都无法踩到坚实的底层,只要陷进去,往上无法攀缘,往下找不到支撑,就会死死地被卡在半腰,全身不能活动,只有最后的绝望与窒息。
现在我害怕突然遇上感觉异常的地方,害怕听到水的飞溅声,我必须尽快离开这危险地带,希望有一片小灌木林来掩藏行踪。万一方向偏斜,奔逃速度在不知不觉问放慢,天光就要重现,东边天际出现鱼肚白,将是我被活捉的时分。
黑夜的黯淡使我无法向远处口望,无法去寻找可以休整和躲避的灌木。
我不能随便钻人哪个洞穴,后面是两条嗅觉极为灵敏的黑狼犬,它们追上来会把两个洞口封死,这样我只能坐以待毙。
前面出现了一片凸起的阴暗部分,不知是山岭轮廓还是树林的暗影?
乌云低垂时常常与朦胧的山岭树林难以区分。无论是什么都必须尽快弄清楚。远处一团微暗的光亮。我目不转睛注视着那团奇异的光亮,觉得它在移动,开始移动速度缓慢,现在明显加快了。
我怀疑是那伙追捕者,是他们点起火把在两条黑犬的导引下一路追来。马灯的灯光在这样的夜晚同样可以使追捕的队伍不至于丢失蛛丝马迹,尤其这无人区的荒野,任何一类印痕都会历历在目。
远处光亮越来越近,我不能长久地飘浮在空中,追捕者当中若是有谁打开雪亮的手电筒,那道划破夜空的光柱就会像枪弹一样准确射中我。他们一旦发现我在空中就会最快地向这里靠近,并有可能一枪把我击落下来。这次的追捕者当中或许就有一位枪手,他们不打算击中我的要害。在瞄准时就打定主意,把我击伤活捉最终推上审判台。
我现在已经悄悄地降落到地面,不敢弄出声响,尽量躬起身子,把双腿屈缩,保持在着地时足以产生理想的缓冲力,尽量使这次降落不惊动周围的一切。
双脚踏上地面时我还是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奔跑声,由近而远渐渐消失,这是我出逃以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发生在我身边的响动,虽然听起来有些像蚱蜢受惊后仓皇蹦跳,但在此时的黑夜里却十分响亮,它那每一个连续的节奏都像鼓声在荒草中响起。
我不敢久留,躬下身用四肢奔跑。
这一片野草并不浓密,也不十分高挺,运用这种姿势奔逃不易暴露目标,后腿用力蹬动使整个身子弹起来,在野草的梢尖上掠过。
一声幽暗的哀鸣从远处传来。好像是饥饿的夜鸟,从那低哑凄怆的鸣叫中,我判断是栖居于岩缝的山枭。这个判断能否给我带来安全的避身处所?
迎面的气流开始凉爽,伴有阵阵腐烂树木的气味。在这个地带,首先出现的应该是古老的橡树林,只有朽死了多年的橡树会发出如此气味。我甚至隐约看见苍黑如铁的千年老橡树的枝干,它们密密匝匝交叉在一起阻挡了我的去路,像来到一座陌生的城下,我试图寻找进入古老树林的人口。
放慢步子,躬下腰身,我小心谨慎地在枝杈间穿行,一点点向树林中走去。浓密而漫无边际的橡树林里几乎不透一丝风,夜色的黑暗和古老树林的寂静,使我有了从来未感到过的慵懒和倦意,连续长时间快速奔跑的疲劳一齐袭来。我终于不由自主地在一棵皲裂的老橡树旁慢慢停下,我需要休息,太累了。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