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又见柿子红
崔志亮
院子里的柿子树,我是许久没有好好看它了。今年深秋,大姐一个电话,说“柿子红了”,我才仿佛被什么牵引着,偕妻驱车回了老家。车刚停稳,推开门,一抬头,便被那满树的景象攫住了心神——已是十月下旬,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剩些疏疏朗朗的,也是半黄半卷,失了精神。唯独那柿子,一颗颗,一簇簇,沉甸甸地挂在枝头,像无数盏小小的、红彤彤的灯笼,在有些萧索的秋光里,静静地燃着。那红,不是一味的鲜赤,也不是单纯的橘黄,倒像是秋霜与夕阳一同熬煮出的、一种浓稠而温润的朱色,衬着高而远的蓝天,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而丰腴的美。我的脚步,不由得就在树下停住了。
这一停,仿佛就踏回了时间的河流里。眼前这“小灯笼”,晃晃悠悠的,便把我晃到了童年。也是这样的季节,空气里满是庄稼收割后干净的草木香。先母便会一面做着活计,一面轻声地念叨起那句我早已听熟了的谚语:“六月鲜桃八月梨,九月柿子烂赶集。”她的声音是软的,带着一点儿乡音的拖腔,像暖融融的棉絮。那时节,柿子是顶好的零嘴儿。偶尔随母亲省亲,外祖父赶河崖大集回来,总会从褡裢里变戏法似的,掏出几颗大大的“烘柿子”给我。那柿子软得透亮,皮儿薄得像一层晕开的霞光,似乎一碰就要破了。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凑上嘴去,轻轻一嘬,一股清甜而凉沁的瓤肉便滑入口中,真真是“吃在口里,甜在心里”。那股子甜,不是糖的甜腻,倒像是把整个秋天最柔和的阳光和最洁净的霜露都浓缩在了一处,由不得你不满足。
然而母亲是从不许我多吃的。她总说,这东西性子寒,吃多了,肚里要长“石头”的。于是,她便有了种种法子来处置这些娇贵的果子。一些品相好的,被她轻轻地码在苑篼里,中间放上一颗苹果或是木瓜,再用布幪上。过些日子,那柿子便被“烘”得软糯了,甜得也更醇厚。另一些,则被她洗净了,放进锅里,用不烫手却极讲究温度的温水“懒”着,说是为了去那涩味儿。这样得来的“懒柿子”,吃起来是脆的,爽爽利利,别是一番清甜的滋味。母亲仿佛一个调度时光的魔术师,她总能将那份得之不易的甜蜜,匀匀地、细细地铺展在一段漫长的日子里。她每隔一两天,才肯给我一颗,说是“打打馋虫”。如今想来,那哪里是打馋虫,分明是将一份短暂的口腹之愉,酿成了悠长的、值得日日期盼的幸福了。
关于柿子的记忆,还有一块是明亮的、陌生的。有一回过年,先父领我去走一家老亲。那位老婆婆的容颜早已模糊在岁月的烟雾里,只记得她盘腿坐在炕上,身后的窗纸透着白茫茫的光。她见了我,笑眯眯地,颤巍巍地从炕沿下的黑瓮里,摸出几块东西来塞到我手里。那东西扁圆的,外面仿佛裹着一层面粉,黑褐褐的,其貌不扬。我迟疑地放进嘴里一咬,口感竟是那般奇妙:软软的,糯糯的,带着一种结实的韧劲儿,在齿间缠绵。那甜,也与烘柿子不同,是收敛的,深沉的,像是被时光风干后留下的精华。
“真好吃!”我含混地说。临走时,老婆婆又用粗糙的纸包了一小包,硬塞进我的衣兜。我注意到那“面粉”沾了我一手,便仰起头,疑惑地问父亲:“大大,她怎么把好吃的放在面瓮里呢?”父亲听了,宽厚地笑了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那不是面粉,是柿霜。是柿子里的甜气,自个儿跑出来结成的。”我似懂非懂,只觉得“柿霜”这名字真好听,像夜里草叶上凝结的露华,带着一种清冷的、诗意的甜。那一小包柿饼的滋味,和父亲那一声温和的解说,便一同成了我童年里一块温暖的、闪着微光的拼图。
后来,人长大了,像一只被风催着走的陀螺,忙于上学,忙于工作,长期生活在被水泥与霓虹包裹的城里。城里的水果摊上,四季都堆满了南来的、北往的、漂洋过海而来的各色珍果,香蕉苹果是寻常,荔枝榴莲也不足为奇。那朴素的、乡野的柿子,似乎便羞怯地退出了我的视野。不知是柿子远离了我,还是我那一颗被俗务填满的心,早已遗忘了它。总之,那一段被柿子的甜蜜浸润着的时光,便仿佛沉入古井的落花,寂寂地,不再有涟漪。
前几年,先父与先母相继辞世。女儿也像羽翼丰满的雏鸟,升学,工作,飞向了属于她的广阔天空。家里忽然间就空了下来,只剩下我和妻子,守着偌大而安静的屋子。老人不在了,老家,似乎也一下子失去了那根最坚韧的牵引线,我们回去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故乡,成了一个名字,一段记忆,一个在电话里与姐姐们互相问候时才会被提及的遥远所在。
大姐的那通电话,像一只无形的手,又将那根线头拾了起来。院子里的柿子树,便这样重新回到了我的生命里。大姐是懂我的,她早就备好了烘的、懒的柿子,我一尝,那熟悉的味道瞬间便打通了多年的隔阂,童年的一切仿佛都回来了。更让我惊喜的是,大姐还用着母亲那般的老法子,将削了皮的柿子用线绳系着蒂巴,一串串地挂在屋檐下,像一道道橙红色的珠帘,在秋风里微微地荡着。她说,这是要晾成“柿枣”,等到春节时吃,比外面买的柿饼更筋道,更有嚼劲儿。我看着那一串串柿子,像看着一串串被小心保存起来的光阴。
今年十月,我正式退休了。生活忽然间换了一种缓慢的节奏。我与妻子便常常驾车,去城外山间寻秋。有一日,信马由缰地行驶在山路上,一个转弯,竟不期然地闯入了一片“柿子谷”。我从未见过那样多的柿子树,几乎是漫山遍野,从山谷一直蔓延到山腰。一棵棵柿子树,脱尽了叶子,只剩下铁灰色的、虬曲的枝干,以一种倔强而又安详的姿态,伸向秋日那碧琉璃似的天空。而就在这万千的枝杈间,缀满了数不清的、红艳艳的果实。那已不是“小灯笼”了,那简直是泼洒开的颜色,是奔腾着的河流,是秋日在大地上奏响的最华美、最热烈的乐章。午后的秋阳,光线是金晃晃的,毫无保留地倾泻下来,照在这些“红宝石”上,仿佛每一颗都在发光,都在燃烧,璀璨得叫人不敢直视。
山谷里热闹得很。许多如我们一般的游人,举着相机、手机,忙着与这壮丽的秋色合影,要将这片刻的绚烂定格成永恒。而当地的人们,则在这片绚烂下从容地忙碌着。他们架着长长的梯子,灵巧地攀在枝头,用特制的竿子小心翼翼地摘着柿子;那一排排专门的晾晒房里,更是橙红一片,人们正将收获的果实,制成柿饼,制成柿枣。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一股丰腴的、甜丝丝的气息。那份忙碌,不是为生计的奔波,而是一种收获的、充满喜悦的庆典。
我立在原地,心中蓦地涌起一阵感动。坡仙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那是江南的秋色;而我们北国的深秋,最不能辜负的,便是这“霜叶红于二月花”与这“柿子红如烈火燃”了。同样是红,枫叶的红,是带着别离与感伤的诗意;而柿子的红,却是一种结结实实的、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圆满。
从童年物质贫乏时代里一颗需要期盼的珍贵零嘴儿,到如今这漫山遍野、任人欣赏采摘的壮丽景观,柿子似乎没变,依旧是那般甜;但环绕着它的一切,却又都变了。我们拥有的越来越多,可那份因为“难得”而倍加珍惜的心情,却似乎渐渐淡了。望着这满山的红火,我忽然明白,越是身处丰饶之中,我们越要学会珍惜。珍惜这自然的馈赠,珍惜这和平的岁月,珍惜那垂挂于枝头、也垂挂于我们心头的一点朴素的甜蜜,与那一段段被它串联起来的、永不复返的温柔时光。
又见柿子红。它红在枝头,也红在记忆的深处,更像一个温润的句读,标记着生命的段落,诉说着岁月的绵长。
2025年11月12日于虞河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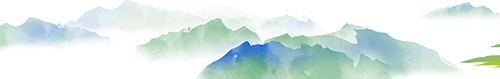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