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文/尹燕忠
故乡的土地饱满丰腴,青葱欲滴的乳汁滋润了蓬勃的生命。向天望苍穹,有晨光的升起,染红江河湖海,正午时光,光临大地,夕阳西下,大地成了胭脂红。
一、故乡土地
我行走在乡村土地上,给黄土亲吻,我浑身熏染了乡土气息,几年来,我走访了几百个乡村,看房屋,探山水。
我痴情于乡村黄土地,迷恋于父老乡亲的土言俚语。那话儿多么亲切柔和,又多么直率刚烈。
乡村是个给钢铁淬火的熔炉。曾经冶炼出多少人才,生产出多少五谷杂粮,麦苗儿青青,孕穗含苞,汁液丰溢,五月金穗黄,挥刀刈穗。麦粒儿滚进了仓里。麦茬里蹦飞了蚂蚱,兔子跃起,刺猬缓缓的爬进苇子河里。可怕的蛇“倏忽”钻进坝堰洞里,正在窥视着什么?
麦茬地里露出了黄土地。
晨曦微亮,百鸟争鸣,啄破了夜的衣衫,人们坡衣起床,套上牲口,开起犁惧,摇耧播种,机器喘起粗气,种子入土,舒服的睡起懒觉,小河里的清水给土地以润泽,玉米粒洗个澡,伸缩身体,不久便窜出沃土,几场雨水泼过,苗子“咔咔嚓嚓”拔节长,场南场西的几百亩玉米抽出了红丝线,绣出了苞米。
行走在乡村大地上,呼吸着乡村的朴素空气,心胸开阔,恬静惬意。
乡村的风景画动起来,牛羊哞咩叫,青蛙欢蹦跳。我多想匍匐在故乡的土地上睡一觉,我的故乡,我的父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睡在黄土之下,我听到了亲人的呼吸。
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哭过,笑过,多少人的血汗洒在这片土地上。
爷爷奶奶受苦了,爷爷挑着粪肥,倒在庄北长方形的大沤坑里,掺和上青草和杂草,经过烈日强光的暴晒,粪坑里喷出强烈的臭气,爷爷和几个劳力又一锨一锨的挖出来,晾干,一车一车运进黄土地上,使上劲了,庄稼推出了丰收的果实,爷爷沧桑的脸上有了笑容,乡亲们笑了!
土地有腿,它在行走,我在故乡土地上行走,时而疾驰,时而缓缓的行走,我在观赏,也在阅读。
我思索着乡村土地上的密码,解读着费解的课题,我看到了鲜亮的大街,图画、标语、宣传栏等等……。
我看到农村的老房屋,好多的黑红色铁木大门紧锁着,门上的对联经过风雨的剝蚀,巳经斑剥。探出墙壁的灯笼在抖瑟,在说什么?南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滿脸皱纹,沧桑纵横,怀着对外出儿女的牵挂,断断续续的说着一些故事。
乡村集市上赶集的老年人一步一步缓缓走着,卖蔬菜的老人期盼的望着一个个行人……。
饿了,吃块煎饼,喝口矿泉水吧,他们默念着,多少挣点钱,不给外出打工的子女添累赘,也好?
阳光泻滿小河的一潭清水,枝头上的喜鹊唱起了歌,喇叭上传来了优美的歌曲,……
二、黄土地,黑土地
故乡的老石碾沉睡着,我听到了滚动的声音,仿佛看到石碾旁挨着号轧粮食的父老乡亲在谈笑风生。
那棵大槐树的技叶间射下日光。月光在碾盘上辉映,这个时候,嫦娥会到人间吗?吴刚还喝桂花酒吗?玉兔跳跃到什么地方去呢?
而生活是美好的,春季里,槐花飘香,丁香树下人影徘徊,蝴蝶扑飞,蜜蜂嗡嗡。
黄土地,乡村的黄泥巴,孕育万物,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那个古屋是明朝武举的二层楼,我攀登上去,身临其境,木制梁檩,古制床箱,院子里有二百多斤重的两个石砘子,一根三米长的木头,一边一个石砘子,那是武举练功佣的东西。
那个小楼,基础是几米高的石头砌垒,下边有拴牛石孔,往上便是土坯砌墙,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雨侵袭,依然坚固,我从土窗台上拿走了一块石头,当做纪念。
童年时,我跟小姨在那个丁字路口上玩耍,一个穿着破棉袄的男人背着我向大街南跑,我有些害怕,他又亲切的把我背回来,一个叫何平的痴女人也给我闹着玩,小姨护着我,善意的把她支走了。
我去过黄河岸边的刘官庄,叔伯姥娘家住在这个庄,村里全是土房屋,屋顶用草苫子搭顶,屋内墙壁用石灰泥的雪白,贴着牛郎织女的年画,亲切朴素而神密。姥娘吃斋念佛,是个接生婆,多少个娃娃从她手中接生。她祀祷人生平安,给人看病治疗。
我看到老人家和善的面孔,听到她柔柔的话语,他念叨着,祝愿我伯父全家吉祥平安。姥娘说,她做了一个梦,梦到石榴花开了,籽粒饱满,果实坠满枝头,一嘟噜一嘟噜的,你大爷全家好起来了。我大爷全家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落户,受到关里坏人的诬陷。不久,应验了,大爷全家安排了工作,坏人受到了惩处。
我看到土墙西边的石榴树真的鲜花盛开,不久我又吃到了石榴。
那个时候,我包过黄河岸边的几个村子,见到村民盖屋子都是用黄土掺上麦稭,把泥搅匀,𣎴要太稀,墙上有掌线的师傅,下边就用铁杈子搓上泥,直接把杈子和泥扔上去,杈子打着旋儿,直接飞到了墙上接杈子人的手上,那人再攥着木头把子,把泥扣在墙上,墙上墙下呼叫着号子,真是黄河岸上的雄壮旋律,那是劳动之歌,也是黄土之歌!
黄土与黑土一个品性,我去过黑龙江省鹤岗市西山区,叔伯哥哥盖屋时也是和关里黄河岸边一个样,用泥垛墙,也要铺上地基,屋顶全用东北草苫盖,燕林哥百巧百能,他在银行下班后,就换上劳动服装,用尺子量好地基,和几个弟兄共同操作,他又会木匠,梁檩椽子都是他打造的,经过加班加点,仅用一个月时间,就盖起了四间大北屋,看上去很漂亮的。
黑土地里含有黄土地的成份,春夏天,鹤岗西山上各种花儿开了,红黄白绿紫,绚丽多彩,引人瞩目。
大爷大娘很勤劳,在西山上开垦了几块长条地,种上了南瓜茄子豆角之类,有时就挎上竹篮去摘拾蔬菜,用以改善生活。
秋后收获白菜和萝卜之类,需要冬藏,有俗话说,黑龙江省寒冷,有冻七不冻八的说法,意思是在山东挖贮藏窖七尺即可,黑龙江就要挖八尺。
需要吃菜时,掀开窖口,腾腾的白气升上来,待半小时下去,用筐子拔上来,那白菜、辣萝卜、胡萝卜鲜嫩嫩的,要淌汁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黑龙江省有大批的山东人,而山东大地又有多少东北人?
热爱黄土地,热爱黑土地,那是我们的热土,哪里的黄土不养人,哪里的土地不埋人?
三、故乡,童年的乐土
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有谁不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我知道,有不少人取小名就叫“土生”,多么稚拙,多么接地气。
吾甫学语,爷爷从黄土地里刨来了花生,母亲在铁锅里用沙土炒熟了,交给瘫痪在床的奶奶,奶奶从床上扔下花生,我便爬着捡起,剥开将香甜的花生果放进嘴里,奶奶笑了。奶奶走了,那年她才56岁。这是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记事哩。
但是,血脉之情永远不会割断。那个年代,刮起了老社员做贡献的风,用墓地百头垒粉坊和梯田。
许多的坟墓被扒开,谁家的坟也无例外。我看到奶奶的尸骨,哭了。父亲去外地建设工程去了。
我去家拿了一个𥱊片子,把奶奶的尸骨一根一根用手拿起放在一个褥子里包上,我眼含泪水,祷告奶奶平安。
那一年我才十二岁,我一个人在东山上将奶奶埋葬,跪拜祭奠,垒起石头坟墓。
一九七八年,辛苦的爷爷走了,我操心修起坟墓,和奶奶合葬。父母走了五年了,我又给老人立起了石碑,铺平墓地供桌前。
每逢十月一和清明节,我亲自上山给老人上坟,填上三锨黄土。
黄土,滋润着万物生灵,也在护佑着逝去的亲人。
小时候,我给土结下了缘分,我𣎴会走时,三四岁趴着走,一手拿一个高梁穗苗子,一边双手扫着地上的尘土,一边偎着向前去,从胡同巷口里趴向前街石碾,趴向石臼,看里边的那洼水,看爬着的蜗牛,它划上了一道道白杠。
小时候有些傻,听老人讲,我趴上西大坑南沿,曾经捏起毛毛虫吃。也曾经撵着追拿镜子照太阳返出去的光,捉不住就哭。
听母亲说,分家时,我拿家来了一个狗食盆子,大人笑得“格格”的。
奶奶给我起小名叫“钢头”,尽管我憨厚一些,但却有坚韧𣎴拔的钢铁意志。大妗子握着我的手软软的,她说,小钢头长大了可下不了力。
其实,我下了不少的力气,当过石匠、饲养员,在场里扬场垛粮食,下过东北,开山采石,手冻裂了,流出了血,出伕时脚冻肿了,所以忘不了翟庄、田山、葛庄、于庄、十里铺。我打过钢钎,凿过垒石,双手握钢锤子把,至今手指弯屈变形,那是那个岁月的光荣。
我拉过地排车,又推过独轮车,那一车车黄土垫进猪牛圈里,猪牛践踏,粪尿杂合,又成了五谷杂粮的好食品。
我推着车子,运输庄稼,脚下腾起飞尘灰土,车辙碾过,印在大地上一些花纹。
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么多的营养。
我上过泰山,走过黄山,跋涉九华山,灵岩寺、千佛山在深情的望着我,与黄土融为一体,那些山上的松柏倒悬绝壁,却把根牢牢扎进稀罕的土里,以豪迈的喉咙唱起生命之歌。
广袤无垠的大海,飞浪走花,荡涤一切,礁石、细沙、蚌壳,无不伴有泥土的气息。
我爰乡土,我爱泥土,尤爰土著,作家孙犁先生是荷花淀派,赵树理先生属于山药蛋派,还有莫言、贾平凹先生无不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黄河岸边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稻花香里说丰年,黄河的波涛捲着黄土一泻千里。
我喜欢在家劳动休息时,仰躺在几米高的坝堰下,闻着太阳晒起的土香味儿,醉了。
那些蚂蚁匆匆运食、蜘蛛结网,小虫虫在荆棘上爬行,一派生命的活泼运动,哼起乡村小曲儿。
我在西林地里看芋头,睡在卧棚里,听小河里的青蛙鸣叫。忘不了在小西园里读过鲁迅先生的书,童年的汁液流淌在我的血脉中。
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我的血液在沸腾,走到老家门口,父母走了,我哭了。
2025.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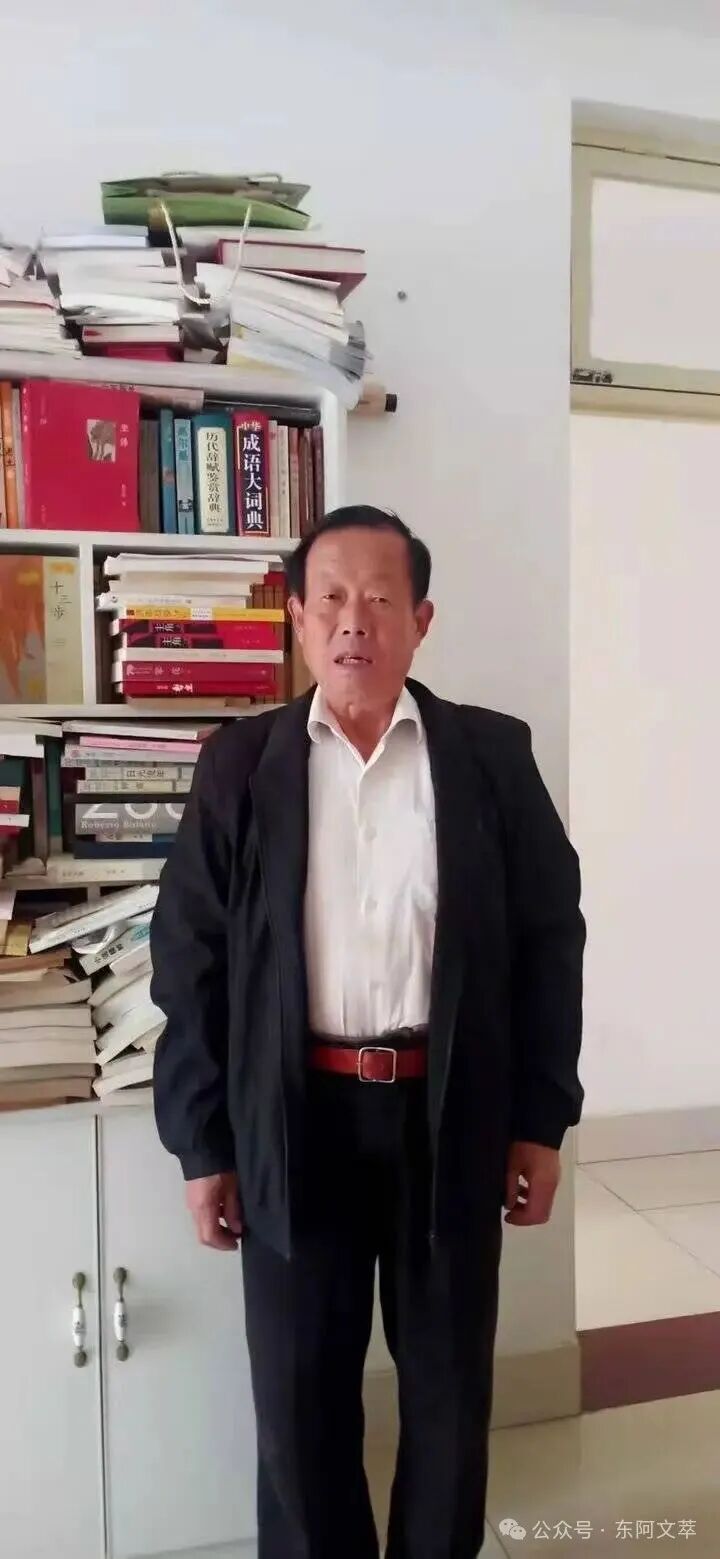
尹燕忠,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一九八三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大众日报、丰收副刊》《济南日报、趵突副刊》《济南时报、海右副刊》,小说《方河的婚事》在“鲁王工坊杯”首届小小说大赛中获得济南日报报业集团、莱芜鲁王工坊锡雕艺术研究院三等奖。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连续获得《大众日报》社全省模范通讯员,连续八年获得《济南日报》模范通讯员。刊物《海棠坞》2023年2期发表小说《三妮儿的杀猪刀子》等发表作品,先后发表各类作品千余篇,主持编纂《安城镇志》《锦水街道志》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