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 踏上奥地利维也纳的第一天
—— 记1988年维也纳的第一顿西餐
作者:陈亚平
一:出发
1988年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远没有如今这样的宏伟壮观,但对于初次来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我来说,见到如此宏伟的机场候机楼,还是感到极大的惊奇和震撼。
当年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不多,飞机也不多,我在候机楼等待上飞机时,从大玻璃窗看出去就能见到飞机。那年我二十四岁,生平第一次看到真飞机,不是从画报里,也不是从电视中,而是眼前实实在在趴在停机坪上的银灰色大飞机,稍远处的天空上还能看到飞机起飞时的景象。
我是1988年3月16日乘坐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航班到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机场,然后转乘奥地利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维也纳国际机场。因为是第一次乘坐飞机,飞机起飞后我就一直透过狭小的机窗俯瞰着祖国的壮丽山河和云海翻涌变化莫测的空中图景,有时真怀疑自己是处于现实中还是处在梦境中。机舱内高鼻梁蓝眼睛的欧洲人占多数,包括我在内只有寥寥几个中国人。
从布加勒斯特到维也纳航程大约一个半小时,傍晚时分,当机翼掠过阿尔卑斯山的残雪,美丽的维也纳渐渐出现在眼前。在晚霞的照射下,一排排起伏连绵富有欧洲特色的红瓦房尽收眼底,就像儿时搭建的彩色积木房子一样,只不过放大了一万倍。
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颠簸,知道自己已经真正踏上了奥地利这片异国土地,心中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与陌生感。
在行李转送带前,我努力寻找着自己那熟悉的红色人造革皮箱,仗着自己年轻力壮,看到红色皮箱和一个背包从面前经过时,一把提起放在机场的行李车上。
看到其他人还在焦急的等待着行李时,我独自推着行李车朝出口走去,远远的就看见姑父吴蓉江和表哥吴杰在海关门外等我。也许印证了得意忘形节外生枝那句话,我刚抬手向他们招手之时,门口内的海关人员伸出手拦住了我,示意我打开皮箱检查。那一瞬间,我心头一紧,仿佛整个空气都凝固了,纵然我明知道自己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但陌生的环境与严肃的眼神以及语言阻碍,还是让初次踏上异国他乡的我心生惶恐。
打开皮箱后,海关人员翻来覆去的查,看到的只是一些餐馆用的小酒具和自己日常换洗的衣物,他拿起小酒具看了看后问我,我却是一脸茫然,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用手势来回答,而他除了叽里呱啦还是叽里呱啦,也许看我态度比较诚恳,同时确实没有违禁品存在,几分钟后示意我检查结束,那颗刚刚还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只觉得经历了一场让人窒息的虚惊。
二:重逢
出了机场海关大门,姑父上来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害怕吗”?还未等我开囗,表哥插上话说“带你去压压惊吃西餐去”。那时的我对于西餐同样也是一无所知,马上能吃到西餐了心里是即好奇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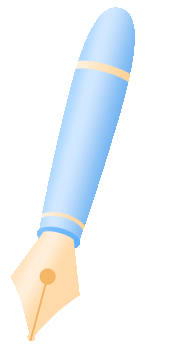
姑父在家乡的县政府部门工作,在家乡时中山装穿得是整洁笔直一尘不染,每件都是经过姑妈仔细清洗熨烫后才穿上的,从不马虎,哪怕有一根短头发掉在衣服上都要先拿掉才让姑父出门,姑妈爱清洁卫生的生活态度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这些晚辈们。今天姑父来机场接我,同样也是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带打得整整齐齐,外披一件呢大衣,虽与在家乡时见惯的中山装大异其趣,但不管是那种衣服穿在他身上都显得那么的合身,从姑父的穿着中就能体现出他平时待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表哥外穿着一件皮夹克,内穿一件羊毛衫,青春英俊的脸庞透着一股干净利落的气质,浑身散发着蓬勃生机。
三:餐厅
我坐进表哥驾驶的小轿车后排,在维也纳城内不知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条街,最后进了一条铺着石块的小巷子里,在一家餐馆的停车场里停了下来。
这家餐馆门口不大也不显眼,门脸窄得只容两人并肩进入,推门进去后看到的是一排供食客悬挂外套的衣柜,另一侧是一面大大的镜子,姑父与表哥分别脱下呢大衣和皮夹克挂在衣柜上,我也学着他们脱下了厚厚的羽绒服,顿时浑身感觉轻松了许多。
推入第二道门后才算是进入餐厅,瞬间暖气混夹着菜肴的香气扑鼻而来,枝形吊灯把光切成碎片,叮叮当当落在白桌布上,暖黄色的灯光围绕在餐厅的每一处位置上,散坐在餐厅内的食客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专心致志的享受着盘中美食。跑堂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马甲在餐厅里来回穿梭,见我们的到来发出了热情的叽里呱啦招呼声,随即姑父指着旁边的一张桌子说“我们就坐在这里”。
不一会儿,跑堂拿来三本菜单递给我们,说了几句话,当然我是一句也听不懂,表哥问我,“喜欢喝可乐吗”,我说“喜欢”,那时国内的可乐可贵着呢!喝可乐的人都属于高收入者,现在能马上喝上可乐,感觉自己已经也是一位高收入者了。
姑父与表哥翻开菜簿看菜单,我也装模作样的翻开,映入眼帘的全是德文字,我看它像天书,它看我可能也像外星人吧!姑父让表哥给我点了一份维也纳炸猪排和一份沙拉。听说要给我点一份,听了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国内去餐馆就餐时,菜点来后都是大家一起品尝,从没听说过要单独给谁点一份菜,独自享用的。一听到炸猪排我的脑子中马上显出猪排骨的形象来,至于什么是沙拉没听过也没见过,心想等会端上来再看吧!
此时跑堂端过来三怀水,我一看那杯黑黑的像酱油一样的应该就是我的可乐了,跑堂放稳三杯水后,同表哥又叽里呱啦了一遍。
经过这叽里呱啦后,总算点好菜了,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大口,凉意直达心肺,一路的旅途辛苦消去了一大半,但心里泛起了纳闷,这老外怎么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中要喝如此冰凉的饮料呀?
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我们的菜都上来了,看着自己面前乳白色的大碗中有西红柿、黄瓜、青椒、红椒及几片生菜,最上面还有一层白色的奶油,似乎也在冒着凉气,这各种颜色的蔬菜搭配在一起非常漂亮,就好像把微型菜园搬上了餐桌,看了使人赏心悦目,我想这应该就是沙拉了吧,而另一盘带有奥地利特色花边的大盘子上,有两片叠加在一起被炸得金灿灿散发着热气的肉排,一边有一大堆的土豆条,再点缀一片西红柿和一叶小草,当然还有一小块柠檬片,造型色彩同样那么美观,我凑过头对着表哥说“这盘菜不是我的,里面没排骨”,表哥一下乐了,指着菜盘说“这就是维也纳炸猪排,你还以为是炸猪排骨呀”!是的,我还真的把维也纳猪排当成炸猪排骨了,因为自己的无知询问,我的脸瞬间一下子就红到脖子上。
四:囧况
我从未见过生菜可以这样直接入口,在家乡蔬菜总要经过蒸炒后才能食用,看着这碧绿的生菜和红彤彤的西红柿,食欲自然也上来了,再加上一路长途颠簸,早已是饥肠辘辘了。我小心翼翼的叉起一片没有碰到奶油的生菜往嘴里塞,稍一嚼动,一股清香带有淡淡的青草味灌满口腔,初次品尝谈不上美味但还能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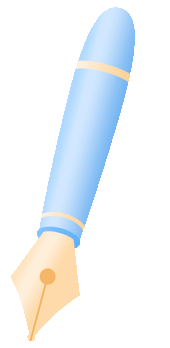
在一旁的姑父看到我这样吃法说“沙拉要先在碗中拌均匀吃才有味道”,说完就直接帮我把沙拉拌起来,看着姑父熟练的动作和他那慈祥的面孔,笨嘴的我嘴巴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在心里面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之情。
被拌均匀后的沙拉,形态早已没有了,但散落其间的奶油被拌散后,一股从未闻过的带有羊腥味的气味直往鼻子冲,当我再次叉起生菜放入口中后,那滑腻的奶油在嘴里翻滚,根本无法咽下去,但口中的沙拉又不能吐出,在两难之际,只好选择强忍着咽下去,此时的我脸色想必己经发白了。
坐在对面的表哥看到我的囧景,冲我挤挤眼压低声音对我说“在国外菜点来后必须要吃完,不可以剩的,这是规矩”。一听规矩两字,没得商量,接下来只好把猪排同沙拉夹在一起吃,来减轻这难闻的怪味。可一份猪排夹着沙拉三下五就吃完了,可碗中的沙拉还剩下一大半,白瓷底像一弯小小的月亮照着我狼狈的倒影。
表哥看到火候差不多了,落出笑容对我说“刚才是忽悠你的,剩下就剩下,没人罚你款”。
一听这话,我赶忙放下手中刀叉推开盘碗,心里却忽地一松,原来远方也有通融。
饭后步出餐厅时,我伸一下懒腰哈一口气,白雾在空中短暂的停留后旋即散去,三月的维也纳还是寒气袭人啊!
望着天空的繁星点点,又扫视了一盏盏已亮起的路灯,跟随着姑父和表哥一起走向停车场,无意间看到姑父把大衣领子抬高了点,在路灯的映照下显得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魁梧。
汽车驶离那家餐馆后,坐在汽车上的我回想起刚才的那碗沙拉,这一刻似乎突然明白;咽不下去的不仅是奶油,更是二十四年来攒下的所有旧味道,而胃里空出来的位置,总得留给未来。



五:后来
在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慢慢的习惯和喜爱上了奶油的香醇,每当舌尖触碰到浓郁的奶油时,总会想起那个面对一碗沙拉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
人们常说味蕾是最固执的记忆,我却觉得,最难忘的是那个笨拙却敢于尝试的自己,咽得下或咽不下又何妨,人生在世,本来就是要尝遍百味才算完整。
2025.1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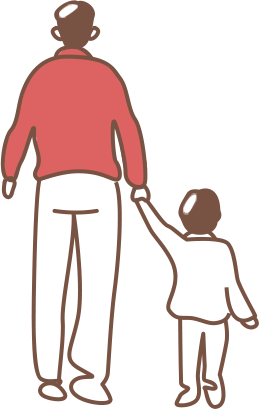
多瑙微诗社编辑部:
社 长:金风玉露
副社长:云惔风轻 秘书长:书含


—END—


多瑙河畔,两三好友,
书写诗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