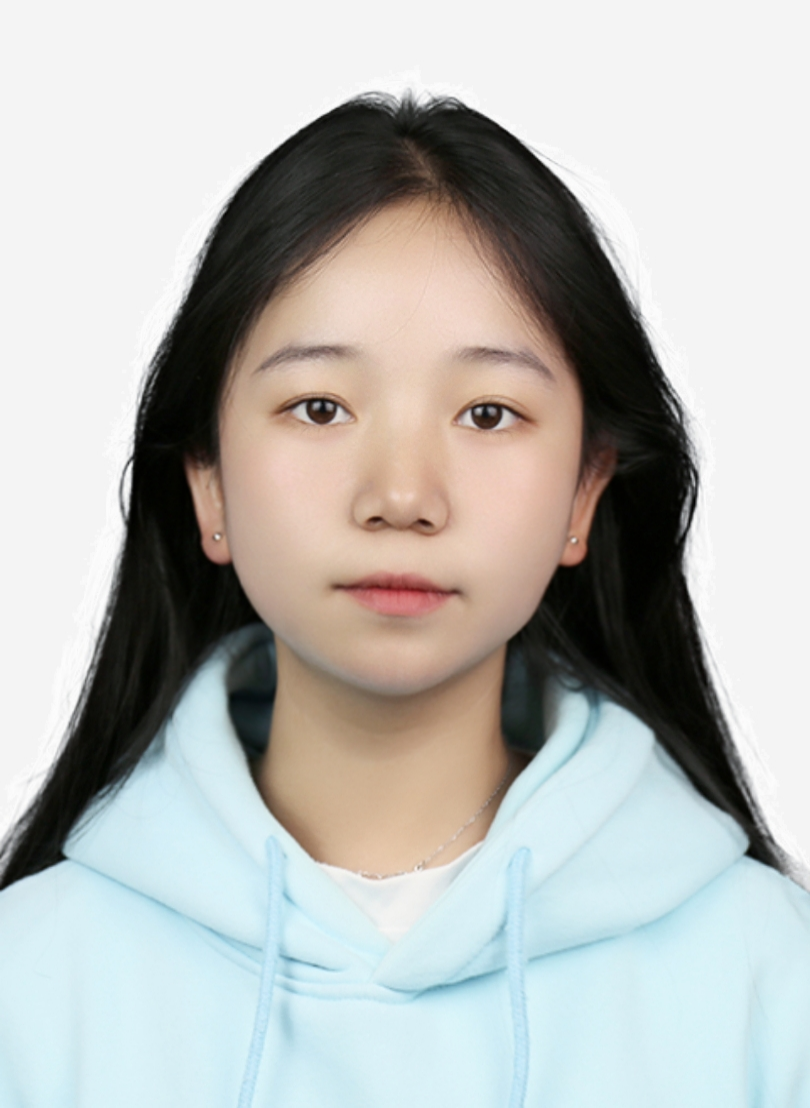
日月照九州,吾乡有清辉
文/柳月
总疑心故乡的肌理里,是浸着日月光华的。它唤作“九州”,名字里就裹着山河万里的浩荡——而我对这片土地所有的眷恋,全藏在朝暮交替的光影褶皱里,一触,便漫出满眶温柔。
破晓的光,是踩着山尖的雾来的。不是城郭里被楼宇切得零碎的晨光,是从东边黛色山梁后,慢悠悠漫过来的金。那金是软的,裹着松针的清、田埂的湿,像母亲刚蒸好的米糕,暖融融地敷在窗棂上。我总爱攥着衣角追着光跑,院中的老槐树还沾着夜露,阳光穿过叶隙,在青石板上绣出细碎的银花。灶台边的母亲正揉着面团,发梢落了几缕晨光,像撒了把碾碎的金箔,她转身时,围裙扫过竹篮里的新摘豆角,连带着光影都晃了晃。田埂上早有农人扛着锄头走,鞋尖沾着湿泥,影子被朝阳拉得老长,一步一步,把希望踩进刚翻好的土里。那时的日头,是活的,是带着烟火气的——它把稻穗烘得暖,把屋檐下的辣椒晒得红,把故乡人的日子,照得亮堂堂的。
暮色是染着霞来的。当夕阳把最后一缕光泼向天际,整个九州就浸在了蜜色里。西天像被打翻了胭脂盒,酡红、橘粉、鹅黄一层叠着一层,连远处的山都染成了淡金的轮廓。村口老槐树下,藤椅早摆开了,爷爷们摇着蒲扇,烟袋锅里的火星明灭,话从去年的收成,说到隔壁阿妹的婚事。我们这群孩子举着芦苇杆跑,把晚霞的影子踩在脚下,笑声撞在晒谷场的麦垛上,又弹回来,混着归巢雀儿的啁啾,成了暮色里最软的调子。我总爱趴在父亲膝头,看他指尖划过天际:“那是火烧云,明儿准是好天。”夕阳把他的侧脸描得柔和,眼角的纹路里,盛着对这片土地最沉的牵挂。等最后一抹霞沉进山坳,月亮就提着银裙,悄悄从东边升起来了。
故乡的月,是浸过井水的清。它不像城里的月,被霓虹晃得蒙着层纱,是透亮的、圆滚滚的——像奶奶腌菜坛里的瓷碗,干干净净悬在墨蓝夜空里,清辉一洒,整个村庄就浸在了凉丝丝的银里。田埂上的稻浪泛着微光,风一吹,就漾起一片银闪闪的波;村口的小河里,月影是碎的,被潺潺流水推着走,偶有鱼跃出水面,“咚”地一声,把满河的月揉成碎银,又很快聚回来,依旧是那轮完整的圆。我们举着纸糊的灯笼跑,烛火在灯笼里摇,把影子投在月光下,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奶奶坐在门槛上喊我们回家,声音裹着月光,软乎乎的——那一刻,连风都是静的,只有月光落在瓦檐上的轻响,和我们踩过石板路的“哒哒”声。
后来我走了远路,在城里的朝暮里打转。清晨的阳光挤过高楼的缝隙,是冷的;傍晚的霞被尾气染得发灰,是浊的;连月亮,都像是隔了层毛玻璃,少了故乡那股沁心的清。可每当加班到深夜,抬头看见窗外的月,就会想起故乡——想起晨光里母亲的发梢,想起暮色里父亲的侧脸,想起月光下奶奶的呼唤。那些被日月浸过的记忆,早成了我骨子里的暖,不管走多远,一触即发。
如今再回故乡,山还是那座山,槐还是那棵槐,只是路更宽了,房更新了——田埂上的拖拉机代替了锄头,村口的文化站亮着灯,可晨光落在母亲发梢的暖,晚霞里爷爷们的谈笑声,月光洒在河面的清,一点没变。我还是会早起追光,傍晚看霞,夜里赏那轮浸过井水的月——原来故乡的日月,从不是转瞬即逝的景,是刻在九州土地上的魂,是藏在每个游子心里的根。
日月照九州,九州藏日月。这被朝暮温柔裹着的土地,有我最亲的人,最暖的时光,最放不下的牵挂。它是我的故乡,是我的九州,是我走多远,都要回头望的清辉所在。
作者简介:柳月,就读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文秘专业,喜欢看小说以及写作,作品《苇叶上的河流》《岁月褶皱里的诗行》曾刊登中华精英文化专栏,并获得“珠江实业智慧人居杯”全国大学生写作创作大赛三等奖和“诗画帽峰·绿美广东”诗文、 征集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