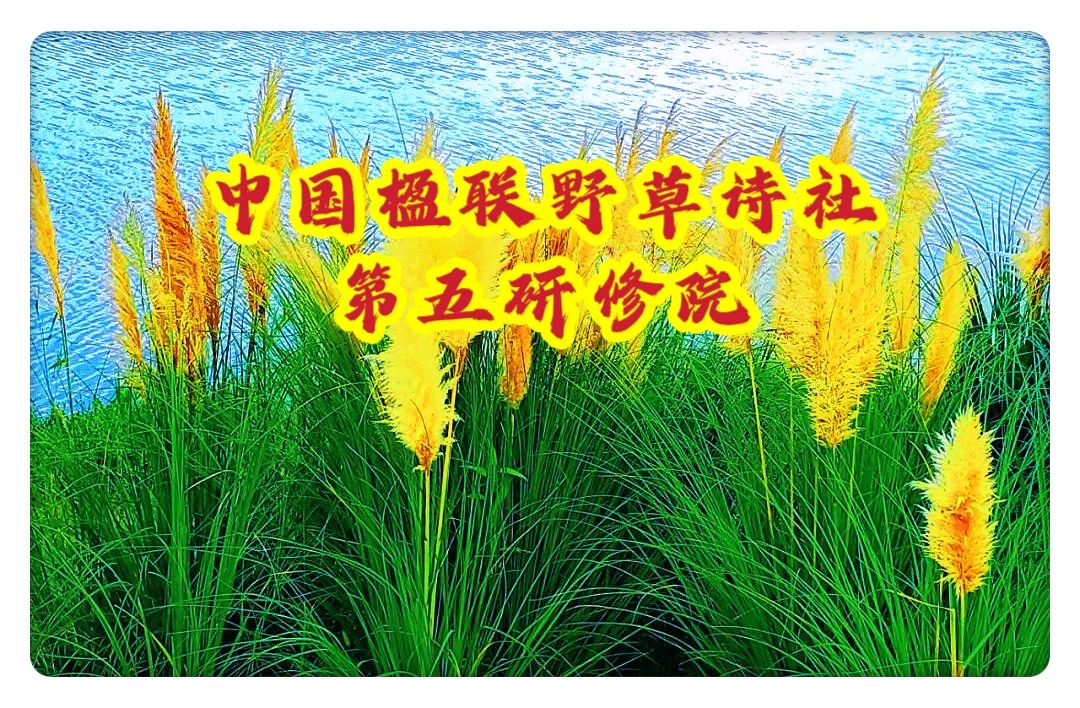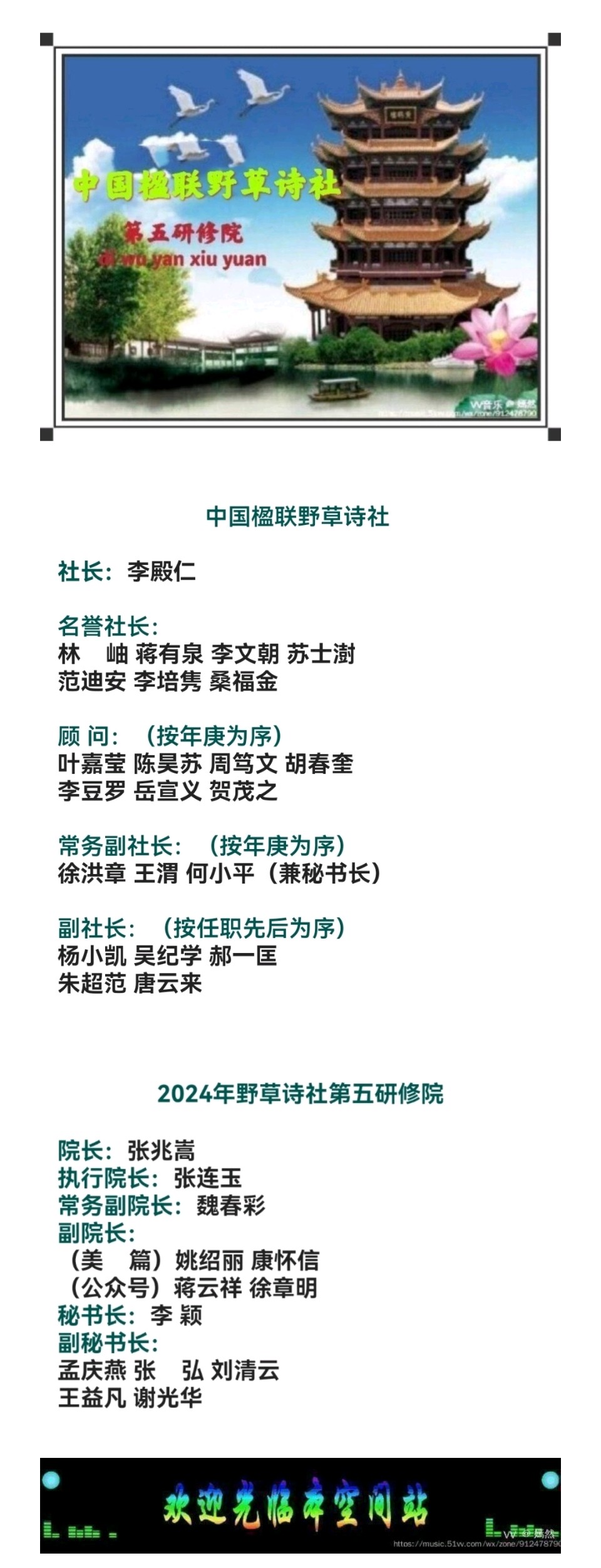红安苕赋
胡世谋(古月)湖北红安
序
红安古称黄安,地接大别之麓,壤带丹霞之温。夫苕者,薯之别称也,闽粤传种,楚地扎根,红安独得天地之秀,故号“红安苕”。自康熙迄今,与斯民共晨昏,历饥岁为仓禀,经战火作糇粮,今则成产业之基,载精神之韵。斯物虽微,实系红安之魂,故为赋以咏之。
正文
一、苕之形质
红安苕者,其貌不凡。皮或丹赤,若晓日初升;或呈金黄,似秋阳泻野。体修长而腴润,质细腻而柔滑。剖之则肉如丹砂,莹然剔透;食之则生脆甜,若嚼霜梨;熟绵香,如啜琼糜。农科院察其质,糖高于常薯,纤维低于凡品,含维生之素,蕴矿物之精,可通腑气,可辅安澜,诚味与养兼者也。
烹饪之法,变幻无穷。蒸则皮红心黄,糯若凝脂;烤则外焦里嫩,蜜流齿颊;煮则清甘入脾,入口即化;晒则脆若金箔,薯香满室。磨粉为面,韧而不烂;酿之为酒,醇而弥香。百法烹调,皆成珍馔,故民曰:“一日无苕,食不甘味”。
二、苕之历史
稽苕之来,远溯明朝。万历癸巳,闽商陈振龙自吕宋携薯种入闽,渐播湖广。康熙间,红安始植,以其地风调雨顺,土疏而肥,遂成特产。《黄安乡土志》云:“藷芋红白二种,生熟皆可食,贫人半岁之粮,多者数十石”。
昔年饥荒,苕为“救命粮”。民倚之度荒,丁壮赖之充腹。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植域延袤二十万亩,岁岁丰登,养育一方。红安人之性,如苕之朴:不图名位,唯务耕耘;不贪膏粱,只甘淡泊,故苕与民,情同骨肉。
三、苕之革命功
及革命烽火起,红安为鄂豫皖根据地之核,苕则成红军之粮。黄麻起义时,民捐口粮,以苕济军,四十二万红安人,献粮千万斤,苕居其半。战士负苕而行,以当干粮;宿营炊苕而食,以振军威。
吴光浩率工农革命军困于山头,三日无食,见山腰苕田,许战士各取二苕,食毕突围,一战而捷。吴焕先领兵过乡,取苕充饥,留银元五饼于地,附书曰:“红军取苕,酬银五块,老乡请收”。此“银元换红苕”之佳话,至今传之。故苕者,非唯粮也,实革命之见证,红安精神之载体也。当时红军三支主力,皆赖苕之滋养,数十万军民,共沐苕之惠,此“革命苕”之名,不虚也。
四、苕之今盛
今之红安苕,非复昔时“救命”之姿,已成“致富”之珍。岁在甲辰(2024),植域达二十八万二千亩,产量六十有三万九千吨,产值四十有七亿五千万。一产十五亿六千万,二产二十七亿三千万,三产四亿六千万,带动七万八千五百农户,共享其利。
加工之肆三十有七,转化之能超三十万吨,制品分八类,凡百二十种:红薯热干面、酸辣粉、倒蒸薯干、红苕酒,皆为佳品。品牌为中国甘薯类首获地理标志者,入“湖北农产品品牌二十强”,价值四十有一亿。商路则线上线下并举:线下设大别山交易中心,联沃尔玛之属,年售四万余吨;线上声播域外,网销十八亿,单品屡登热榜。更出口欧美,与美商订粉丝三百吨,值六百六十万;四品过中欧之检,将销欧盟,海外粉丝四千余,声名远播。
五、苕之精神
夫苕之德,索寡而献丰。不择硗薄,不畏旱涝,落地即生,岁岁报稔。红安人之质,如苕之朴:革命时“一要三不要”,舍生取义;建设时“一图两不图”,埋头苦干。故“红安苕精神”者,即奉献之精神,实干之精神也。
苕与红安,同呼吸,共兴衰。昔为救荒之粮,今为振兴之基;昔伴红军历风雨,今随百姓奔小康。它非独一薯,实红安之根,历史之镜,精神之旗也。
乱曰
伟哉红安苕!生乎红土,长乎红乡,献乎红民。貌不矜贵,而功盖一方;质不华艳,而德润千秋。昔济饥馑,今富山乡;昔哺红军,今耀华邦。愿其香飘四海,誉满九州;愿其精神,代代传扬!
歌曰
红安苕兮,丹皮赤心。
生于大别兮,沐彼晴阴。
养我百姓兮,岁稔年丰。
助我红军兮,气壮山河。
今兴产业兮,利泽万民。
苕魂永在兮,光照前程!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