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点击头像 关注我们

【编者按:这篇访谈录整理拟稿于2023年8月。《找字庄村志》是六汪镇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编纂团队攻坚克难,破解 “史料缺、记忆散” 的难题,自2017年启动至2020年,仅三年时间就完成编纂,并通过评审出版发行。这部志书资料考证严谨,采用 “纲目体” ,分门别类地梳理记录村庄自古至今的发展变迁历程。
《找字庄村志》不仅是一部 “历史档案”,更是村民的 “根” 与 “魂”—— 村民能从中读懂家乡如何从明洪武二年一路走来,发展成为如今的 “青岛市级美丽乡村”;在共同参与编纂的过程中,村民凝聚起共识,乡村建设也由此有了可参考的文化坐标。
2023年8月21日,本文采访人前往找字庄村,在村志主编王安君家中,就村志编纂相关问题与他深入交流,随后整理形成了这篇访谈录。
王安君,男,1944年12月出生,1972年1月至1998 年 12月担任找字庄村党支部书记,2017 年出任《找字庄村志》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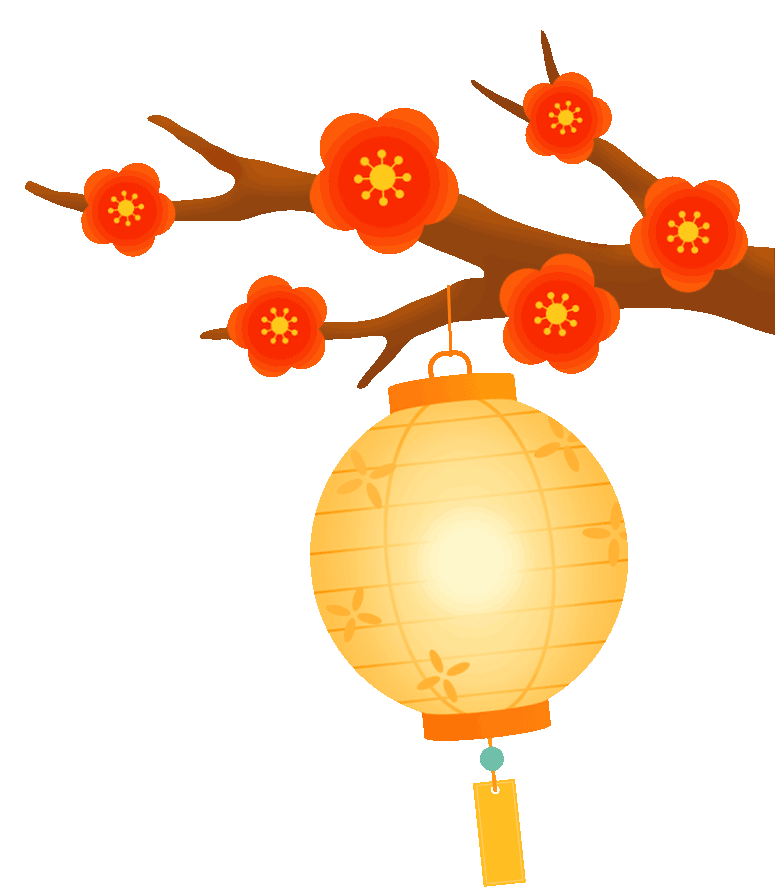
—— 访六汪镇《找字庄村志》主编王安君

《找字庄村志》封面
采访人:王主编,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找字庄村志》的基本情况?
王安君:好的。《找字庄村志》于2017年8月启动编纂,2020年4月完稿,历时近三年。全书共60万字,分为概述、大事记、基本村情、姓氏人口、政治、经济、文教、卫生、民生、风俗、人物、附录等十余部分。经六汪镇人民政府审定,作为青岛西海岸新区史志丛书,由线装书局于 2020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
采访人:您曾长期担任找字庄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找字庄村志》主编。当初是如何萌生编纂这部村志的想法的?
王安君:找字庄村自明洪武二年(1369年)立村,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然而村里始终没有一部系统的史志典籍。从古至今,村情信息主要依靠老人口口相传,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历史断档。因此,纂修村志十分必要。当时,青岛西海岸新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也在积极鼓励乡村修编史志。村 “两委” 认为,将村里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人物事迹等内容系统记录下来,既能让村民明晰 “根在何处”,又能总结过往发展经验,为未来乡村建设提供借鉴,推动乡村进一步发展。于是,村里下定决心启动村志编修工作。
采访人:编纂一部村志,首先需要搭建完善的组织框架。您能否介绍一下《找字庄村志》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与分工情况?比如当时是否设立了专门小组负责不同工作?
王安君:我们在2017年8月成立了村志编纂委员会,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培林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统筹全局工作;我和王展林担任主笔。委员会下设五个专项小组,各司其职:信息收集组专门负责入户采访村民、前往档案馆查阅资料;外联组负责对接新区史志研究中心、六汪镇政府,争取专业指导与工作支持;保障组承担编纂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顾问组邀请村里的老人及在外工作的乡贤参与,协助核实老一辈的历史史实;撰写组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整合,形成志书初稿。整个编纂过程并非依赖一两个人的力量,而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
采访人:资料收集是修志工作的基础。找字庄村历史悠久,但早期史料留存较少,当时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通过哪些方式克服了这些困难呢?
王安君:最大的困难是 “老史料稀缺、老记忆零散”。在老史料方面,除了古代《胶州志》和现代的《胶南地名志》中对 “找子庄” 有零星记载外,村里没有可查阅的文书档案;而老一辈人的生活经历,也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能零散回忆起来。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 “入户访谈”。我们先后入户采访知情村民260多人次,将这些口述资料完整记录下来,并通过多渠道交叉印证,将其作为志书拟稿的重要素材。二是 “档案查阅”,多次前往青岛西海岸新区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40多份与找字庄村、六汪镇相关的历史资料,精准核对村庄建置沿革、重大事件的时间线。三是 “物证征集”,对于村民家中的老照片、老农具等物品,我们逐一上门收集,前后共征集到800多幅图片,逐步拼凑完整村庄历史的 “拼图”。

位于村东北路口的村标(2023年摄)
采访人:提及村名,有资料显示存在 “找子庄” 和 “找字庄” 两种说法。村志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您在核实过程中,是否发现了更倾向某一种说法的证据?
王安君: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展开了深入讨论。清道光《胶州志・建置》、民国《增修胶志・疆域》中均记载为 “找子庄”。因有人到村里寻找儿子,故得名 “找子庄”。这是正史中的记载,不能忽视。而村里代代相传的却是 “找字” 的传说 —— 相传送信人在村里丢失书信,又返回来找到,于是,村里长者便提议将村名定为 “找字庄”。村里的长辈们都认可这一说法,这是村落的 “活记忆”,也应当记录下来。最终,村志采用 “双说并录” 的方式:先记载正史中的 “找子庄” 说法,并注明史料出处;再记录 “找字庄” 的民间传说。至于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为准确,我们没有下定论,也难以给出确切结论。将两种说法并列呈现,为后人留下考证空间,这也体现了修志 “存真求实” 的原则。
采访人:志书的体例与内容设置至关重要,《找字庄村志》采用 “纲目体”,分为概述、大事记、基本村情等十几部分,当时为何会做这样的安排?
王安君:我们是在新区史志研究中心的指导下,结合找字庄村的实际情况确定的体例 ——“纲目体” 采用横排门类的方式,先设置 “类目”(如 “政治”“经济”“文教卫生”),再下设 “分目”(如 “经济” 类目下细分 “农业”“工商业”“集市贸易”“财税”),最后以 “条目” 形式细化具体内容。这种体例条理清晰,便于读者快速查找所需内容。在时间跨度上,志书从村庄立村一直记载到 2017年12月,坚持 “近详远略” 的原则。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村庄的发展变化最为显著,村民感受也最为深刻,且这一时期的资料留存最为完整,因此这部分内容成为村志的重点。
在特色内容方面,一些类目均有体现,如“风俗”“人物” 等。“人物” 部分,除了收录革命英烈孙怀义、王乾林的传略外,还收录了村里处级以上干部的简介,既能缅怀革命先烈,也展现了村庄人才辈出的实况。此外,对于 “特色地名”,如沙帽沟、翻车沟等,尽管无人知晓其具体来历,但这些地名都是村民生活的印记,我们也专门将其列出,希望能留住这些珍贵的 “乡土符号”。

村东桥(2023年摄)
采访人:您认为《找字庄村志》编成后,对找字庄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比如在文化传承、村民凝聚力提升等方面。
王安君:我认为最大的意义在于 “留根” 与 “聚心”。“留根” 是指,志书梳理了村庄历史的发展变迁脉络 —— 先祖何时迁来、村里何时通自来水、何时获评 “青岛市级美丽乡村”等信息,均有明确的时间记载和完整细节,子孙后代翻开志书,就能清楚了解家乡的发展历程。“聚心” 则体现在编纂过程中,村民们共同回忆历史、提供资料,甚至会为 “某件事具体发生在哪一年” 展开讨论,这种参与感让村民们的归属感显著增强。此外,如今村里开展文化建设、打造美丽乡村景观时,也会参考志书中的相关资料,避免盲目建设。可以说,这部村志不仅是一部 “历史档案”,是村里发展的 “参考手册”,更是连接村民情感的 “精神纽带”。

村内大街(2023年摄)
采访人:《找字庄村志》从2017年8月启动到2020年完成,历时三年。在这一过程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安君:在资料征集过程中,许多村民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不畏艰难、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事迹,这种奋斗精神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此外,乡贤们的支持也令我十分感动。初稿完成后,我们将其寄给在外工作的乡贤,每位乡贤都逐页仔细批注,有的还补充了自己掌握的资料,甚至有乡贤专门从外地赶回村里,与我们核对细节。应我们的请求,找字庄村籍人士、曾任新华社拉美总分社社长的王进业,还欣然为村志作序。这种 “全村人共同为村志出力” 的氛围,让我深刻感受到,这部志书并非一部普通的书籍,而是大家共同的 “乡愁载体”。
采访人:您拥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亲身参与了村志编纂,对于村志编修工作,您是否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王安君:谈不上经验,只是有几点心得体会。第一,一定要 “发动群众”。如果仅依靠少数人,难以收集到全面的资料,志书撰稿工作也会举步维艰。第二,资料要 “多方核实”。老人口述的内容可能存在偏差,档案记载也未必全面,必须通过多种渠道交叉印证,确保资料的准确性。第三,要有 “耐心”。修志是一项细致的慢活,不能急功近利。遇到资料缺漏的情况,甚至需要暂停撰稿,重新寻找线索、挖掘资料。只有耐住性子、下足功夫,才能保证志书的质量。第四,要“接地气”。村志并非学术著作,应撰写村民能看懂、感兴趣的内容,少使用晦涩术语,适当搭配老照片、老地图等,提升村民的阅读兴趣。
采访人:最后想问问您 —— 现在再翻开《找字庄村志》,您最喜欢翻阅哪一部分?为什么?
王安君:我最喜欢翻“大事记”和“人物传略”。翻阅 “大事记” 时,就如同重新走过一遍村庄的发展历程,心中感慨万千;翻阅 “人物传略”,看到孙怀义、王乾林等英烈的事迹,便会提醒自己,不能忘记这些为国家牺牲的先烈。


“都市头条·乡村记忆”主编日月星辰,男,生于1962年8月,高密市阚家镇人,曾在诸城市任职,退休干部。现居青岛西海岸新区,《六汪镇志》副总编辑、六汪镇文学艺术联合会顾问。


“点点赞”再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