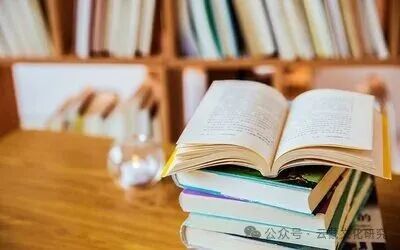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琼庐玉语·山居书香”(吴琼小小说读书会)系列稿件之九
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琼宇清辉映人间
文/王宇鹏(陕西商州)
当“纯文学式微”成为文化界的集体隐忧,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碎片化阅读主宰、快餐式写作泛滥、消费主义文学大行其道的当下,那些典雅庄重的纯文学究竟去了哪里?吴琼的小小说,恰如琼楼玉宇间洒落的清澈月光,既照亮了当代文学的灰色地带,更以文学家的良知,观照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与当代文学的精神困境。他的文字清雅洁净,不依托宏大叙事,却能在尺幅之间承载物质时代的精神叩问;他的家国情怀远离流量喧嚣,却能用细腻笔触探触人性的幽微之处与社会痛点,映照社会转型中个体的命运浮沉与精神困境,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严肃的道德思考与深刻的思想批判。
《瓊廬文集——小小说卷》堪称小小说文学版图上的一座醒目标识。文集依题材分为校园、旧味、小城、红尘、哲思、人间六大板块,以多维视角写尽世间百态。吴琼的创作深深植根于洛南山水风情与人文底蕴,宛如从这片土地自然生长出的文学精灵——以精炼篇幅承载丰厚的人生悲欢,在有限空间中勾勒各色人等的命运曲线,将洛人的淳厚、洛水的清灵,以及乡风民俗与市井街巷的生活气息,内化为灵动深远的叙事情味。他的文字扎根河洛文化土壤,源清流洁、雅正干净;笔下那些在时代变迁中徘徊、挣扎与坚守的平凡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坚韧不屈、内心矛盾与拼力抗争,无不折射出洛南人特有的生命气质与文化底蕴。正是这种对地域文化的深沉凝视与艺术升华,让他的创作超越了简单的地域书写,触及普遍的人性困境与精神求索,使“洛南故事”拥有了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他不仅标注了洛南小小说的艺术高度,更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地域文学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范本。
当代文学的核心使命,在于与现实同频共振,而非构筑脱离生活的空中楼阁。当下不少文学作品与现实关联薄弱,缺乏对时代脉搏的真切把握。一些作家闭门造车,以虚妄的文字概念建构虚幻的海市蜃楼,美其名曰先锋写作;而吴琼的小小说始终以“微观个体”为切入点,精准捕捉社会转型中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隐痛,让文学既真正融入时代,又超越现实的局限,成为关切社会痛点,将深层次社会问题放在大众视野的聚光灯下,让文学照亮现实人生。吴琼聚焦底层群体的生存艰难:打工者在拥挤的出租屋里计算着微薄薪水。为生计疲于奔命者在亲情与生存的困境里苦苦挣扎,用矛盾的精神尺度丈量生命的宽度。《父母的开关》一文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的两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子女因忙碌等原因,对父母的关心常常处于“关”的状态,很少主动关心父母的生活和需求,即使回家也往往只是匆匆而过,没有真正关注到父母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的爱却始终处于“开”的状态,无论子女如何,父母总是无条件地关爱和付出,甚至在自己面临困难时,也不愿给子女添麻烦,默默承受。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在情感和关心上的不对等,形成了老人与子女之间关于孝亲与疼爱的亲情之间的双重困境:空巢父母无意麻烦忙于事务的儿女拾掇开关,以石头压住拉灯绳,点了一个月的煤油灯;而子女又在现实生存困境里无意间关住了孝亲通道情,当直视父母生存的困苦之时,又充满苦恼、自责与无奈。吴琼的文学现场不刻意渲染苦难,却以最本真的生活原貌,还原了城市化进程中边缘群体的真实境遇;他挖掘日常生活中的隐性困境:欲望与人性的撕扯、职场中的无形歧视、中年人的生存压力、道德与理性的纠结,都隐藏在“一通沉默的电话”“一件未能送出的礼物”“一句无奈的祝福”等细节中,让读者在熟悉的生活片段里,看见那些被忽略的现实矛盾。《浇花》并未直接批判城市的冷漠,而是通过主人公对文竹的疏忽,引发读者对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反思——在快节奏生活中,人们被物质与虚拟世界包围,忽略了内心对真实情感与精神寄托的渴望,文竹的枯萎恰是城市虚拟文化侵蚀现实情感、精神家园逐渐荒芜的隐喻,揭示了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漂泊。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方式,恰如《电影》中对普通人命运的刻画:不追求史诗般的恢弘,却让时代变革在个体的悲欢中悄然显现,使文学与读者的生活经验产生深刻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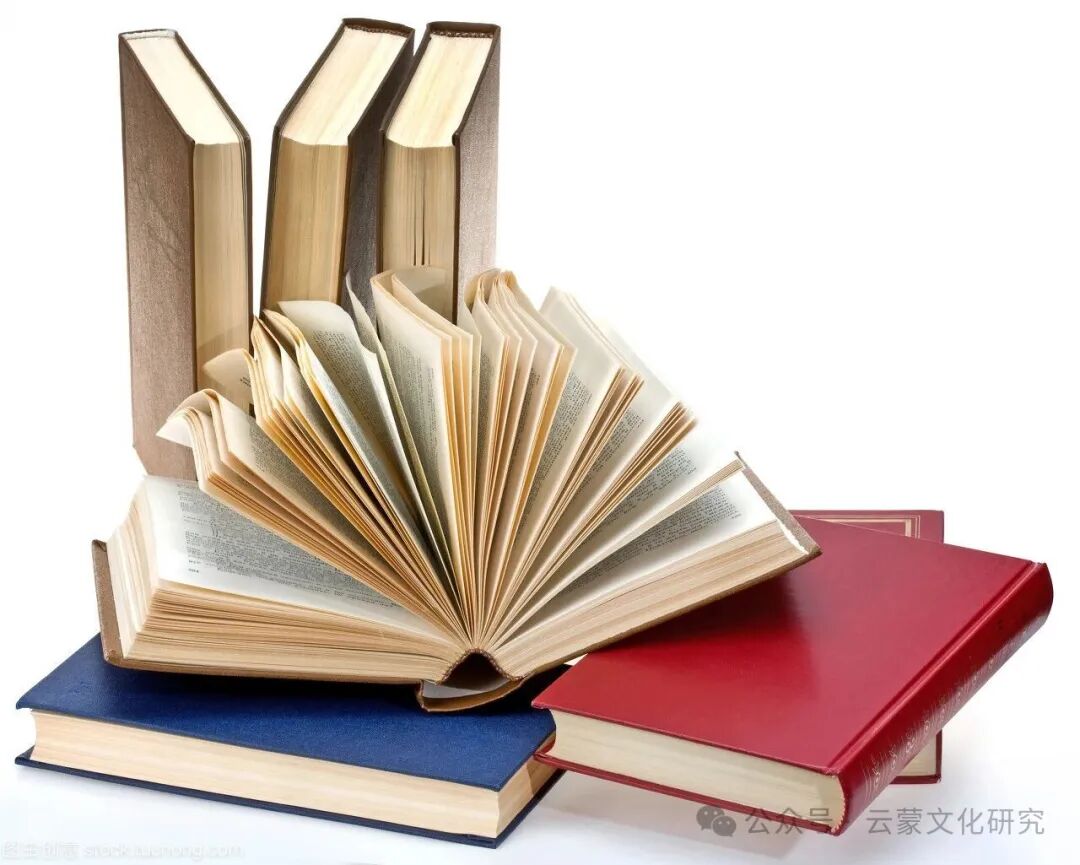
在快节奏的消费时代,文学不应沦为宣泄焦虑的渠道,更应成为抚慰心灵、传递希望的精神纽带。吴琼的小小说从不回避现实的痛感,却始终以克制的温情溶渗人性的光辉,让读者在困境中看见希望的微光。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带着“不完美的坚韧”,展现乡土情怀与现代文明进程的交织碰撞。《1983年的雨鞋》通过“藏雨靴”“恳求同学家长别再叫孩子‘雨鞋’”等细节,刻画了一位为守护孩子尊严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底层父亲,在贫困年代的窘迫中,凸显出底层家庭的尊严与深沉父爱,反映了物质匮乏与精神需求的矛盾;《远逝的纸鸢》以纸鸢为象征,讲述乡村教师转型为城市投资商的人生历程,在城乡流动中展现个体命运的起伏——爱情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消逝,映射出转型期个体命运的分化与人生遗憾;《一里一里的阳光》中,少年扛着椽木换取小人书的情节,既体现了贫困年代底层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与不屈的韧性,也道尽了乡土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浇花》里秦歌沉迷于城市网络情感、忽略阳台文竹的细节,再次印证了虚拟文化对现实情感的侵蚀,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迷失。这些作品凭借细腻的细节与具体的物象,让乡土质感与时代印记交织,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深刻呈现了时代变迁中底层民众的命运浮沉与精神世界。
面对碎片化信息对深度阅读的冲击,当代文学更需以精湛的艺术手法,重建读者对“慢阅读”的耐心与信心。吴琼的小小说将“方寸之间见精魂”的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丰富小小说表现手段提供了宝贵借鉴。鱼得水是《你以为你是谁》中的主人公。他是洛城四大才子中唯一成名后没有去省城而留下来的人,是洛城文学圈里的一面旗帜,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他看到乞丐冲他翘大拇指,误以为乞丐认识他时,会主动打招呼,后来发现乞丐并非针对他,便自嘲地摇头,体现出他对自身名人身份的在意。当得知有人用他的名字开饺子馆、网吧时,他觉得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了侵犯,想要去告对方,反映出他对自己名声的珍视以及内心的虚荣。在互联网普遍的时代,鱼得水一开始还是用自来水笔和方格稿纸写东西,后来在儿子的鼓动下才买电脑并学会在电脑上写文章、发邮件、建博客,这表明他在适应时代发展方面相对滞后。他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却发现更多的是一个笔名叫“鱼得水”且名声很坏的小子的信息,这让他感到气愤和无奈,他的留言被对方回怼,进一步凸显了他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处境。吴琼以鱼得水为主人公的系列小小说,折射出小城小文人的文化精神追求与现实利益的冲突,多侧面折射出当代文人的名利挣扎和心灵困惑。《生命的颤音》是一篇构思精巧、意蕴深长的小小说。它用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触及了生命、死亡、爱与尊严这些永恒的命题,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在读者心中奏响了一曲悠长而震撼的旋律。文章通过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启迪人们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哲学探讨。歌颂了生命在终点前的尊严,最终肯定了精神与艺术在超越肉体苦难时的伟大力量。那颤抖的、微弱的、行将消失的声音,恰恰是生命本身最真实、最深刻、最动人的乐章。
这个时代需要的文学,不是迎合流量的快餐,而是能够扎根现实、传递温暖、精耕细作的“精神滋养”。西方文化入侵下传统道义的分化和资本倾轧下乡村文明的消融,致使当代人文化精神断裂和宗族根脉遗失,让漂泊的游子失去生命的原乡。《倒塌的老房子》是我们成长中的原乡记忆。文章以老房子为线索,表达了对父母、家庭和故乡的深厚情感。老房子是父母白手起家的见证,是家族命脉赓续的物质载体,是当代游子魂牵梦萦的精神寄托。它的倒塌象征着岁月的流逝和亲情的永恒。作者通过回忆与老房子相关的往事,如想给父母拍照、为老房子留影等未实现的心愿,以及大哥在危难时刻的相助和离世,展现了亲情的珍贵与无奈,传递出对亲情的眷恋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吴琼将中国式乡愁具象化,引发漂泊的游子深度思考人生的来路和去路,找寻灵魂栖息的精神巢穴。吴琼的小小说无须制造舆论热点,却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出路,以微观叙事承载现实重量,以人性温情抚慰心灵焦虑,以精湛艺术守护阅读的深度。
文学的价值从来不是功利性的,它不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却能让我们在喧嚣中看清内心,在困境中理解他人,在时代变迁中坚守生命的精神追求。正如吴琼笔下那些坚守的平凡人物,当代文学也需在浮躁的环境中,坚持对现实的关切、对人性的尊重、对艺术的敬畏,如此方能在纯文学式微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为读者营造一片可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