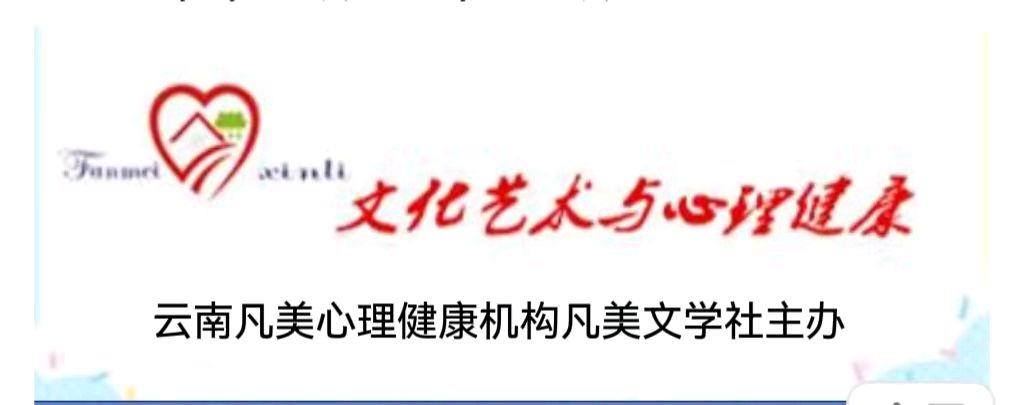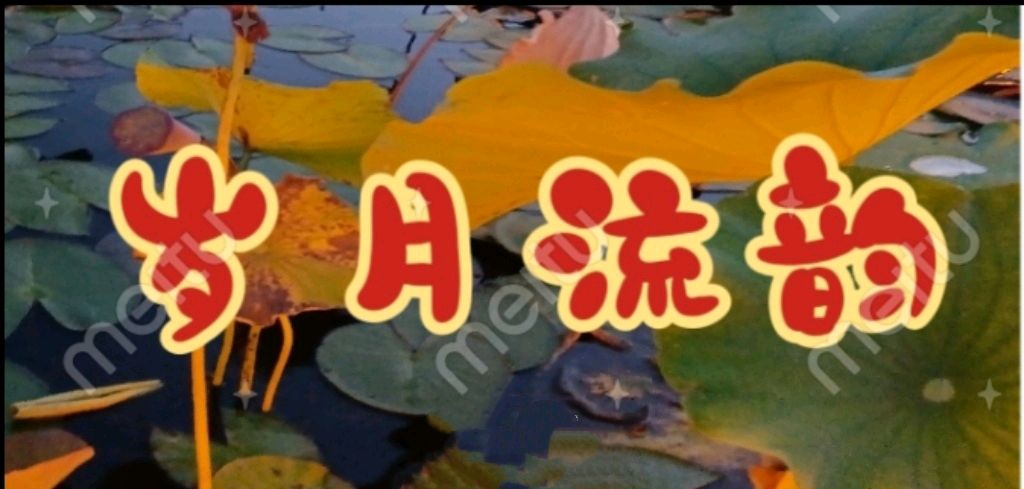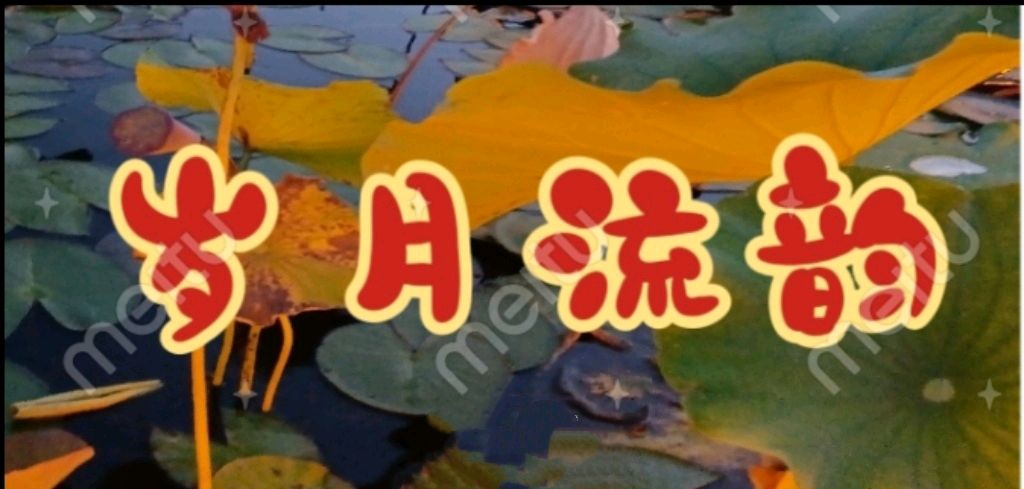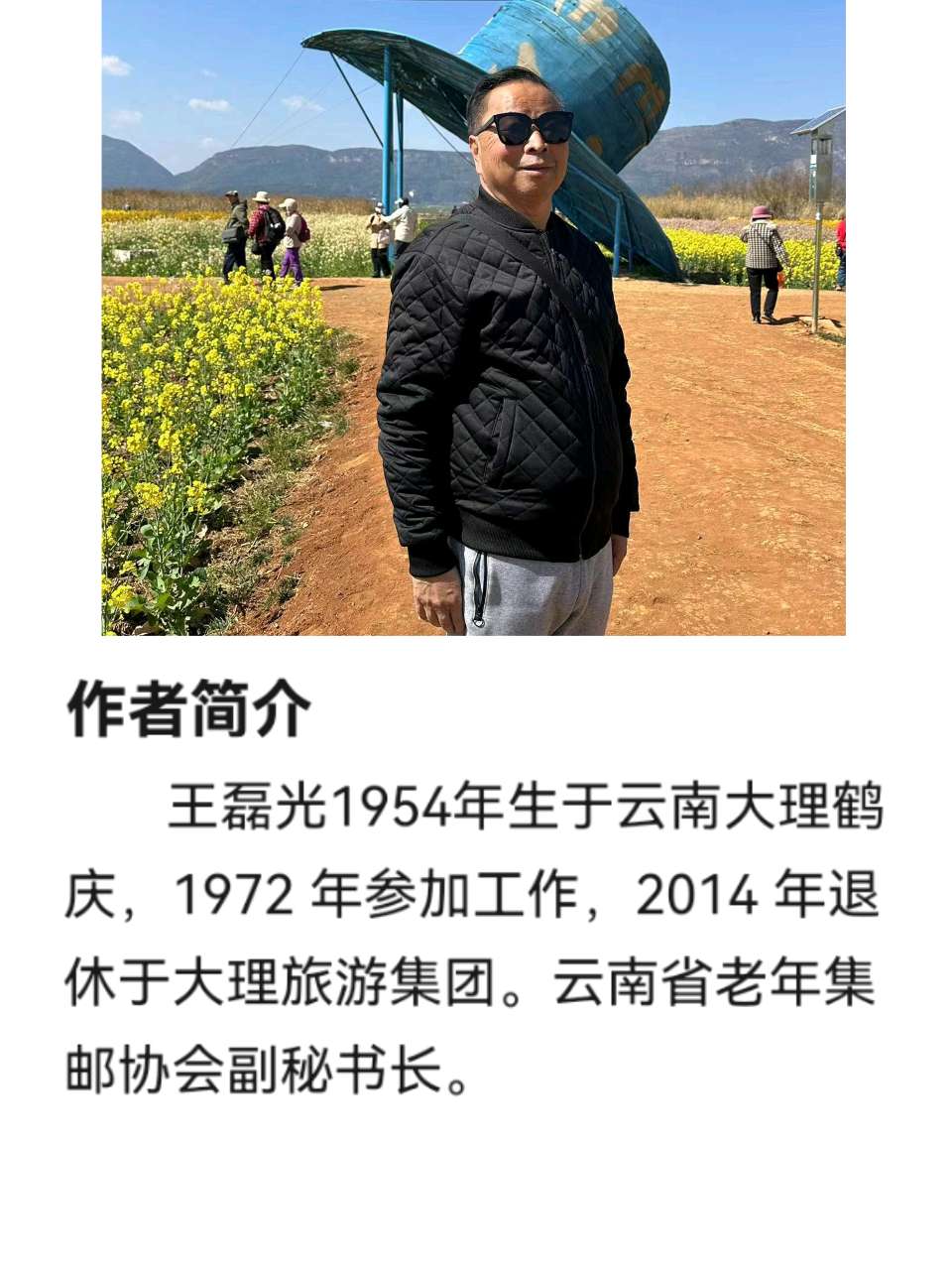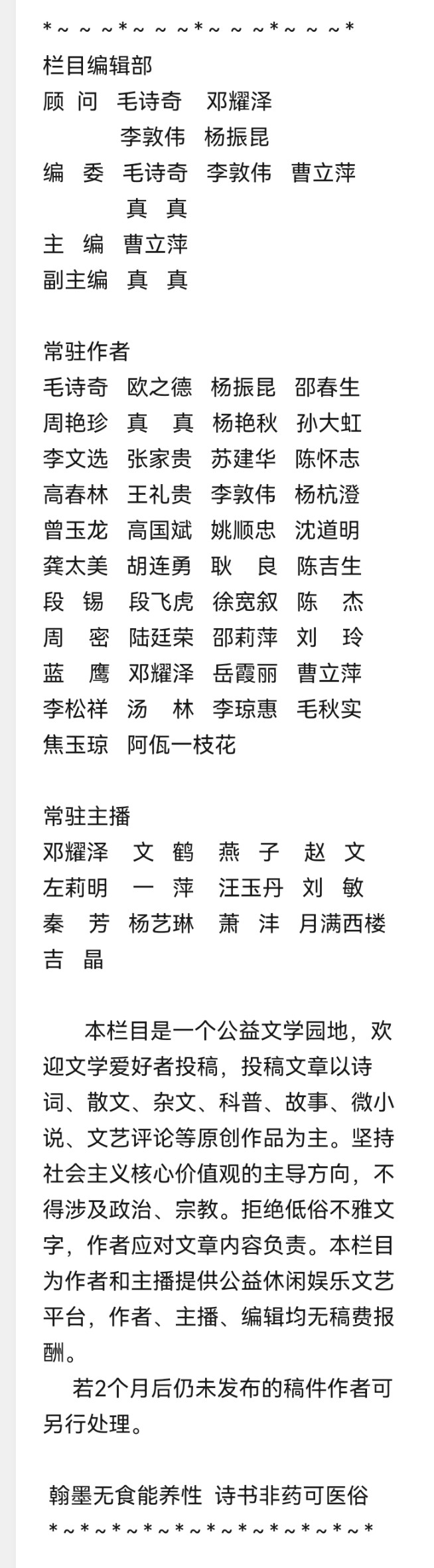岁月流韵征文之四
作者:王磊光
父 亲
如今,我们竟也到了白发盈头的年纪,膝下孙辈已如当年自己那般顽皮跳脱。然而每当深夜独坐,灯影摇摇之际,父亲那熟悉身影却总在眼前浮现,心绪便如江水涌起,难以平静——原来父亲早已逝去在七十年代的光阴里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从未消褪。
他年轻时做过小学老师,我尚记得他立于讲台之上,手中紧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奋力书写,字迹清晰有力,如刀刻斧凿。他边写边讲,言语虽常被剧烈的咳嗽打断,却仍然竭力挣扎着继续下去。教室里粉笔灰便如雾霭般弥漫,他忍不住的咳喘之声,仿佛在静寂中撕开了口子,如风箱般呼呼作响,声音沙哑急促,回响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学生们都仰着小脸,眼睛里亮晶晶的,分明地映着他们王老师那喘息不止的瘦削背影。
后来,父亲竟放下教鞭,转而去做了建筑工人。他每日早出晚归,奔忙于工地与家庭之间。我常见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身上沾满泥点汗渍,衣服上的补丁洗得发白,针脚细密整齐,如同他教过的方方正正的字迹。他蹲在屋外台阶上,一根根数着散乱的钢筋,手背上的青筋,因长年累月的劳作而凸起盘结。夕阳沉落,他攀爬在脚手架上的身影,在暮色中愈来愈模糊,最终竟被黑暗全然吞没了。有时,他干完活回来,哮喘病发作,便蜷缩在床角,胸口激烈地起伏着,喉咙里发出断续的嘶鸣,那声音如同破旧风箱艰难拉动,每一声都沉重地压在我们心上。
然而父亲还有另外一副神采飞扬的面目,他热爱滇戏,尤其擅长扮演丑角,在舞台上,他是众口交赞的“王老艺人”。台上的他,仿佛换了个人,虽然脸上涂满油彩,却挡不住眉宇间闪动的光芒;他身披彩衣,插着翎毛,脚步轻盈,动作滑稽,引得台下笑声连连。可每每戏演完,他躲进后台,我总能听见那熟悉的喘咳声,如暗处呜咽的风,从幕布缝隙里渗出——台下笑声越热烈,那喘息便愈发急促,仿佛是生命在戏谑与重负之间艰难地换气。卸妆时,他对着镜中那张抹去油彩后显出苍白疲惫的脸,默默凝视良久,竟似在辨认一个陌生人的面孔。
他肩上担着的,是一家人沉沉的日子。白日里他在工地上奔走,夜晚又赶往剧场登台。他脚步匆匆,如被无形之鞭催赶着,终年无歇;两处营生之间,只余下那断续的、令人揪心的喘息声,在昼夜之间艰难地循环往复,犹如命运之绳勒紧了他单薄的躯干。他这样苦苦支撑着,直至耗尽最后一息力气,最终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如幕布悄然垂落,永远告别了舞台,也告别了人世。
如今我的小孙子时常翻动旧物,他翻出父亲当年演戏时用过的那顶丑角帽,帽上两根翎毛依旧挺立。孩子好奇地举在手中挥舞,阳光穿过窗棂,恰好照亮了翎毛顶端,绒绒的细毛在光线里跃动,闪烁着细微的金色光芒。
我嘴唇微动,却终究没有出声——几十年流光里,父亲那副在生活重压下从未弯折的脊梁,那在喘息间隙里挣扎而出的笑声,原来早已化为血脉中无声的盐粒;纵使岁月消磨,纵使生活之海潮涨潮落,那盐粒沉淀于灵魂深处,依旧硌痛着记忆,又悄然滋养着我们余生的年轮。
他走得越久,身影却越清晰;那喘息与笑声交织的声响,竟在我血液里日夜奔流——父亲肩头扛着砖瓦和生计的担子,背上驮着全家的重量,但生命之盐却正于如此沉重中无声结晶:它从不教人垮下,只将背影铸成路标,叫后人沿着他未竟的苦途,继续迈步。
~~~ ~~~ ~~~ ~~~
中秋之夜
月是分外地圆,分外地亮,像一只毫无瑕疵的银盘,冷冷地悬在墨蓝的天绒上。清辉洒下来,却不带什么暖意,只将院落里的砖石、将远处疏疏的树影,都镀上了一层薄薄的、苍白的银。四下里是静的,邻家的笑语与杯盘的轻微碰响,隔着墙壁传来,渺茫得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独独我们这一方小院,浸在这片过分明亮、因而也显得格外清寂的月光里,仿佛成了一座孤岛。
我的思绪,便不由得被牵回到许多年前那个同样被月光照得透亮的中秋夜去了。那时我还小,只觉得那夜的空气里,绷着一根看不见的、紧得快要断裂的弦。父亲已病了些时日,屋里总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药味,混着一种生命渐渐流逝的、无可奈何的气息。然而那一夜,他的精神却似乎好得出奇,竟挣扎着要坐到院中来。母亲和我们拗不过他,便扶他坐在那张旧藤椅里,用厚厚的毯子将他裹得严严实实。
他仰着头,静静地望着那轮月亮,望了许久。月光洒在他瘦削得脱了形的脸上,那高耸的颧骨和深陷的眼窝,便在光影下显得格外分明,有一种触目惊心的雕刻感。他忽然转过头,用极微弱、却极清晰的声音对我们说:“今年的月亮,真好。”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那时无法理解的光,不是欢喜,也不是悲伤,倒像是一种了然的、疲倦的平静。他又喃喃地说,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我们听:“只是……太亮了,亮得有些晃眼。”
那时我全然不懂这话里的意思,只觉那夜的月亮确是亮得异样,将父亲的身影在青石板上拉得又长又淡,仿佛随时都要化去一般。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种告别。是一种灵魂在远行前,对尘世最后、也是最用力的凝视。那过分明亮的月光,于他,或许正是一条通往不可知世界的、苍白的路。就在那个中秋过后不久,父亲便像被秋风吹熄的烛火,静静地走了。从此,中秋的月亮于我,便永远地失去了它圆融欢庆的本意,而染上了一层清冷与决绝的底色。
月光无声地流泻着,将我从回忆的深潭里轻轻托起。院角那株老桂树,在风中微微摇曳,投下些破碎而凌乱的影子,像谁的心事,铺了一地。我端起桌上的茶杯,茶是刚沏的,温热的雾气在冷亮的月光里袅袅上升,旋即便散得无影无踪。这温热与这清冷,恰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忽然想起另一位亲人,我的嫂子,她便是在另一个中秋夜,悄无声息地睡去的。她走得更安详,像一片秋叶,在月圆之时,静静地归于尘土。一个节日,竟这样郑重地、不容分说地,承载了两代人的逝去。这月圆,于人世间的团圆,真是一种尖刻的反讽了。
我抬起头,再一次凝视那轮月亮。它依旧是那般圆满,那般光辉,遵循着千古不易的轨道,冷静地俯视着这片大地。它见过秦皇汉武,也照过李白杜甫;它成全过无数花前月下的盟誓,也抚慰过更多客舍羁旅的愁肠。它是不朽的,因而也是无情的。它并不为哪一个人的悲欢而改变分毫。父亲的离去,嫂子的长眠,于它漫长的生命而言,不过是微尘般的刹那。它今夜这样圆满地亮着,明年,后年,千百年后,它依旧会这样圆满地亮着。
而人呢?人却是这般渺小,这般脆弱。我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这亘古的月光下,显得那样汹涌澎湃,又那样微不足道。我们总爱将人间的情绪,寄托于这些恒久的事物,盼它们能带来慰藉,殊不知,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淡漠。这淡漠,并不冷酷,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律,如同春去秋来,潮涨潮落。
夜渐渐深了,风里带了些许寒意。隔壁的喧笑不知何时也已歇下,世界重归于一片广阔的沉寂。只有那轮月,还是那么亮堂堂地挂着。我心中的那份不安,似乎在这冰凉的月华里,被洗濯得淡了些。它并未消失,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更为深沉的东西。我忽然觉得,父亲和嫂子并未真正远去,他们只是化成了这月光的一部分。往后每一个中秋,无论我身在何方,只要抬起头,便能看见他们——在这片无所不在的、既带来思念也带来抚慰的清辉里。
这光辉,从此便成了我与逝去的亲人之间,一种无声的、永恒的言语。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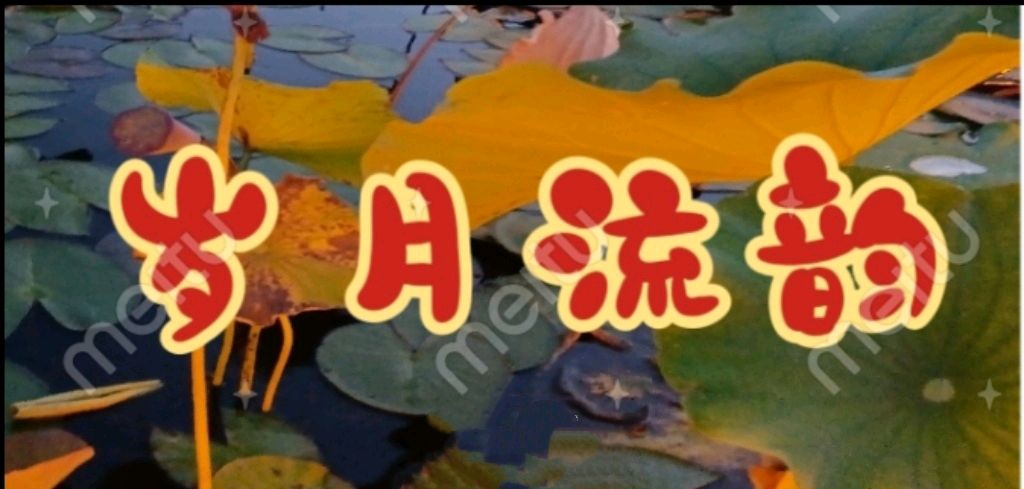
《岁月流韵》文集征稿启事
《岁月流韵》文集现向银发族老同志们发出邀请,请用您的生花之妙笔,撰写锦绣文章,将您宝贵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以回忆录、散文、随笔、书信体等形式展示出来,给我们的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后辈儿孙,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创新未来。
征文内容与要求如下:
一、 内容主题:
1. 存史资政:记录珍贵的历史细节与个人体悟,为后代留下真实生动的时代注脚。
2. 交流互鉴:促进老同志之间的思想交流与情感共鸣,共享人生智慧与生活乐趣。
3. 启迪后学:用您的故事与经验,教育激励年轻一代珍惜当下、奋发有为。
4. 陶冶情操:丰富晚年文化生活,在笔墨书香中涵养性情,乐享晚年夕阳红。
二、体裁形式:散文、随笔、短篇纪实、书信体等均可。篇幅不宜过长,散文、随笔2000字左右,短篇纪实控制在5000一10000字以内为宜。
三、 稿件要求:
真实性:内容须为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力求真实准确。
健康性:内容积极健康,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原创性:投稿作品须为本人原创,未公开发表过(或在特定范围内征得同意后可转载,作者应对所投文稿内容及文字负全责,除错别字外,编辑不作仼何修改)。
投稿格式:标题+姓名+原创投稿
(不按格式要求投稿的不予采用)
四、评优奖励
截稿后,栏目将根据阅读量,点赞点评量,并请专业评委评出优秀作品给予奖励。(注:编委评委均不参与评奖)
投稿微信:guyu6464
截稿日期:2026年8月31日
《文化艺术与心理健康》编辑部
2025年9月19日
欢迎企业、机构和个人赞助支持公益
~~~ ~~~ ~~~ ~~~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