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琼庐玉语·山居书香”(吴琼小小说读书会)系列稿件之六
于烟火处见众生百相
——《一里一里的阳光》多维价值解析
文/寒梅飞雪
最早认识吴琼先生,大概在十几年前。那时候都流行用博客写文章。在博客里,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名叫江东璞玉的人写的文章,是关于洛南县城农贸市场拆迁后那份不舍的感情。我就关注了他,浏览了他博客里很多文章。瞬间就被吸引了,他的文字很朴实,总能从无数的小细节中解剖人性深刻的一面。情感细腻,细节描写入木三分,非常接地气。大多都能够引起我们六七十年代人的共鸣、共情。瞬间感觉特别亲切。我们就在博客里进行了交流。原来他真名叫吴琼,就住在东街蝗虫庙福音堂附近。无形中,我们心里的距离就拉近了。
有一次,我到农贸市场去买一双护士鞋,刚好碰到了一个长得像吴琼的人在鞋摊面前看书。我试着问了一下,果然是他本人。吴老师长得高高瘦瘦的,人非常和气,也很内敛。但说起文字来满心满眼都是喜爱,谈起他的小小说和散文写作,毫不拘谨,娓娓道来。人和他的文字一样,非常朴素,真诚,接地气。我们交流甚欢,就互相加了QQ。临走,吴老师还送了我他的散文集《半个苹果的爱》。后来得知吴老师到北京去了,加上各自工作繁忙,我们交流的就少了。
这次听说吴老师要在中秋举办读书会。遗憾的是我还在南京交流学习,不能亲临现场。我只能在遥远的南京预祝吴老师读书会圆满成功!
吴琼的《一里一里的阳光》作为一部聚焦底层生活的小小说集,以“亲情、言情、都市、荒诞、百姓、校园、市井、官场”八大主题为骨架,将个人记忆与时代印记熔铸于208篇短章之中。作品既延续了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独特的叙事智慧,在方寸篇幅里构建起立体的人间图景,其谋篇布局的精巧性、艺术特色的辨识度、思想内涵的厚重感与教育意义的启发性,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坐标系。
一、以真实的情境构建生活全景
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小小说“单篇独立”的散点结构,采用“主题聚类+人物勾连”的双线布局,形成兼具整体性与开放性的叙事网络。八大主题如同八块拼图,每一块既承载着特定领域的生活切片,又通过“底层人物”这一核心线索相互咬合——乡村题材中的“茂才”(《父亲的大学梦》)与都市题材中的“叶叶”(《虚拟死亡》)虽身处不同空间,却共享着“为生计奔波”的生存底色;官场题材里“万老与老万”的身份嬗变,与市井题材中“沅好吾”的偏执计较,又共同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价值错位。这种布局让作品脱离了“短篇集”的松散感,成为一部微型的“社会生活百科”。
在单篇内部,作者善用“以小见大”的结构术,以一个细节撬动整个人生的重量。《1983年的雨鞋》以一双廉价雨鞋为线索,串联起贫困年代的尊严困境:“我”因雨鞋被同学嘲笑而辍学,父亲为买雨靴向供销社主任低头,最终用“一家人半个月吃稀饭”的代价换来了儿子的体面。文章未直接写贫困的残酷,却通过“雨鞋—雨靴—父亲的妥协”这一链条,让时代的沉重感透过纸面渗出。《父亲的大学梦》更是巧妙勾连起不同时代的教育与就业困境:一方面还原六七十年代父母“以苦力托举子女求学”的众生相——茂才近五十岁仍在工地“挑砖、和灰、拉沙”,工资一发就寄给上大学的儿子,还坚信“娃念书是正事”,只因自己“小学没上完就种地,吃了没文化的亏”;另一方面又暗合当下就业现实——如今即便985、211院校抛出橄榄枝仍有学位空缺,榆林师范学校、商洛学院的公费生录取分数线飙升至612分、590多分,与当年茂才“以为儿子上大学就能摆脱苦力”的期待形成强烈反差,一篇短章横跨数十年,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命题在时代变迁中更具思辨性。又如《纸戒指》,以一百枚纸戒指为载体,将青春期的羞涩、错过的遗憾与成年后的释然浓缩其中,开篇“折戒指”的甜蜜与结尾“拆戒指见字迹”的酸涩形成闭环,短短千字却完成了对“青春遗憾”的完整叙事,尽显结构的张力。
作品在布局上暗藏“记忆线索”:开篇“1983年的阳光”与后记“乡村,我文学的根”形成首尾呼应,将个人经历转化为集体记忆。校园题材中的“少年扛椽买书”(《一里一里的阳光》)与百姓题材中的“秋实收苞谷”(《秋实》),虽相隔数十年,却都延续着“劳动换希望”的精神内核,让整部作品成为一条流动的“时光河”,读者既能在单篇中捕捉瞬间的感动,也能在通读中感受时代的变迁。
二、于“烟火叙事”中凸显艺术特色
吴琼的叙事风格兼具“泥土的粗粝”与“诗意的细腻”,他擅长将生活中的“烟火气”转化为文学意象,让平凡场景迸发出审美张力。在《思乡酒》中,“粗瓷酒缸”成为乡愁的载体:“父亲在火塘里添上桦栗木,用二尺长的火筒吹燃,在‘哔哔啵啵’的燃烧声里,拿下烟黑色的搭钩,把盛满水的铁壶吊在熊熊的火焰上”,这段描写没有华丽辞藻,却通过“桦栗木、火筒、搭钩”等具象,勾勒出陕南乡村的生活肌理,让“乡愁”不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可触可闻的烟火气息。
人物塑造上,作者摒弃了“脸谱化”写法,善用“细节留白”让人物立体鲜活。《丁大夫》中的老医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通过三个细节立住形象:一是“胸前总挂着听诊器,撩起病人衣服在胸前这儿听听,那儿按按”,显其严谨;二是“处方写中文名,还在某些药方前做记号:‘这些药到医院外边买,便宜’”,显其仁心;三是“把推不掉的礼物换成副食送到病房,给农村病人”,显其悲悯。三个细节层层递进,一个“不唯利、有温度”的医者形象便跃然纸上,比长篇大论的赞美更有说服力。《父亲的大学梦》中对茂才的外貌刻画,更是将“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发挥到极致:当茂才得知儿子因找不到工作醉酒打架,“出现在工地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以后了,他明显地黑了,瘦了,胡子更长,头发更白,话更少了”。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没有长篇大论的感慨,仅“黑、瘦、长胡子、白头发”几个朴素的形容词,便勾勒出一位老父亲的沧桑——他曾将“儿子上大学”当作摆脱苦力命运的希望,如今希望落空,连“话更少了”的细节,都藏着价值认知被打碎后的迷茫与无力,读者仿佛能亲眼看见这位“老黄牛”般的父亲,在生活打磨下佝偻的背影,这种“以形写神”的笔法,让人物的心酸与落寞直击人心。
语言风格上,作品融合了陕南方言的质朴与书面语的凝练,形成独特的“乡土诗意”。《美子》中写日本媳妇融入中国乡村:“美子做好饭,先端给公婆、丈夫,最后才给自己和孩子盛。给祥云端饭、端水、递东西都是恭立、弯腰、低头、举案齐眉”,“恭立、弯腰”等词语保留了传统礼仪的庄重,而“吸溜吸溜喝糊汤”又充满生活气息;《狗事》中“王大毛喊了一声:‘黑豹,走!’”,短短几字,既写出人物的蛮横,又暗含对“人与狗”关系的讽刺,语言的精准度与张力尽显。

三、体现以“底层视角”叩问时代精神的内涵
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以“小人物”的命运为镜,照见了转型期中国的精神困境与价值坚守。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作者没有刻意美化或批判现实,而是通过人物的选择,呈现出人性的复杂与坚韧。《儿子的谎言》中,年轻人为给父亲买鞋,恳请店主配合“演戏”,店主最终被感动,“掏出99元递过去”,这个情节既写出了贫困年代的无奈,更凸显了“孝心”与“善意”的温暖力量,让读者在感动中思考“物质与情感”的轻重。
作品对“身份焦虑”的书写,更是触中了时代的痛点。《所在地》中,乌有道为办作协入会手续四处盖章,农村不认他“无土地”,小区不认他“户口在农村”,最终只能伪造“无稽城乌有社区”公章。这个荒诞的情节,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身份困境——既失去了农村的根,又未被城市接纳,成为“悬浮的人”。类似的还有《虚拟死亡》中的叶叶,“在城市,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是农民;在农村,没有耕种一寸土地”,这种身份的撕裂,正是无数农民工的真实写照,作品通过他们的故事,让“底层”不再是抽象的标签,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
《父亲的大学梦》则进一步深化了“教育与命运”的思考:茂才“累死累活供娃念书”,坚信“上大学就能摆脱下苦力的命”,这种朴素的期待,是上一代人对“知识价值”的集体信仰;而如今大学生就业难、公费师范院校分数线飙升的现实,又让“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变得复杂。作者没有给出答案,却通过茂才“儿子大学毕业仍去酒店打工”后,“又带着女人来工地,只为供女儿上大学”的选择,展现出底层家庭在时代变迁中的韧性——即便期待落空,仍未放弃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种“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正是底层人物最珍贵的品格。
此外,作品对“权力与人性”的反思也极具深度。《官场生活体验馆》以虚拟体验的形式,揭露了官场的潜规则:“一小时就是外边的一年,你可以兢兢业业工作,也可以上下钻营地跑官”,而最终“从正门走出去的好官”,竟是因母亲的电话唤醒了良知。这个结局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指出“权力诱惑”与“人性本真”的永恒博弈,让读者在荒诞中思考“为官者的初心”。《“同意”获奖》则更具讽刺意味,县长的“同意”二字获书法特等奖,甚至被用作酒店、宾馆的招牌,这种“权力美学”的泛滥,正是对“权力异化”的辛辣批判。
四、蕴含于“生命叙事”中传递精神力量
作为一部扎根现实的作品,《一里一里的阳光》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承载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能让不同群体在其中找到精神共鸣与成长启示。对青少年而言,作品中的“奋斗叙事”能激发向上的力量:《一里一里的阳光》中的少年,“扛着一丈长的松木橡走三十五里地,只为买小人书”,他“走一里地歇一次脚,额头上、脊梁上涂满汗水”,最终“腰杆挺得笔直,像个得胜的将军”。这个故事没有说教,却让“坚持”“行动”的道理变得可感可知,比空洞的励志口号更能打动人心。《父亲的大学梦》中茂才的经历,也能让青少年理解“教育机会的珍贵”——上一代人曾为“能读书”拼尽全力,如今拥有更优越学习条件的年轻人,更应懂得“珍惜”与“奋斗”的意义,即便就业有挑战,也需像茂才那样“不放弃”。
对成年人而言,作品中的“情感叙事”能唤醒对亲情、友情的珍视。《谁还记得我的生日》中,吴天昊忙于生意,忘记自己的生日,最终是母亲的电话提醒了他:“今天是你的生日,别忘了吃长寿面”。这个细节戳中了许多人的痛点——我们总在为“生计”奔波,却忽略了最珍视我们的人。作品通过这个故事,提醒读者“别让忙碌偷走亲情”,这种启示比任何“亲情教育”都更具冲击力。
对社会而言,作品中的“底层叙事”能唤起人们的共情与反思。《难看》中的狗剩,因长相丑陋被拒绝穿园林制服,却默默打扫卫生到最后;《回头客》中的“神经病”女人,只因店主把她当人看,便坚持到这家店购物。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底层人物的尊严往往藏在细微的善意中,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体现在对“边缘人”的态度上。这种对“平凡人”的尊重,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一里一里的阳光》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底层生活的褶皱,也照见了人性的光辉。它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小小说”的形式,完成了对时代的记录与反思;它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烟火气”的书写,让文学回归生活的本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部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应当扎根大地、贴近众生,于平凡中见深刻,于细微处见真情。我们常常会在这些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命运,反思自己的生活,引发深刻的人性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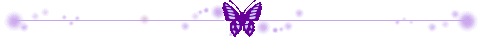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寒梅飞雪,教育工作者。喜欢在烟火气里涂涂写写,于平淡生活里感受岁月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