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叶延滨|选择诗歌就是选择一种命运——读卫国强史诗《到虞乡》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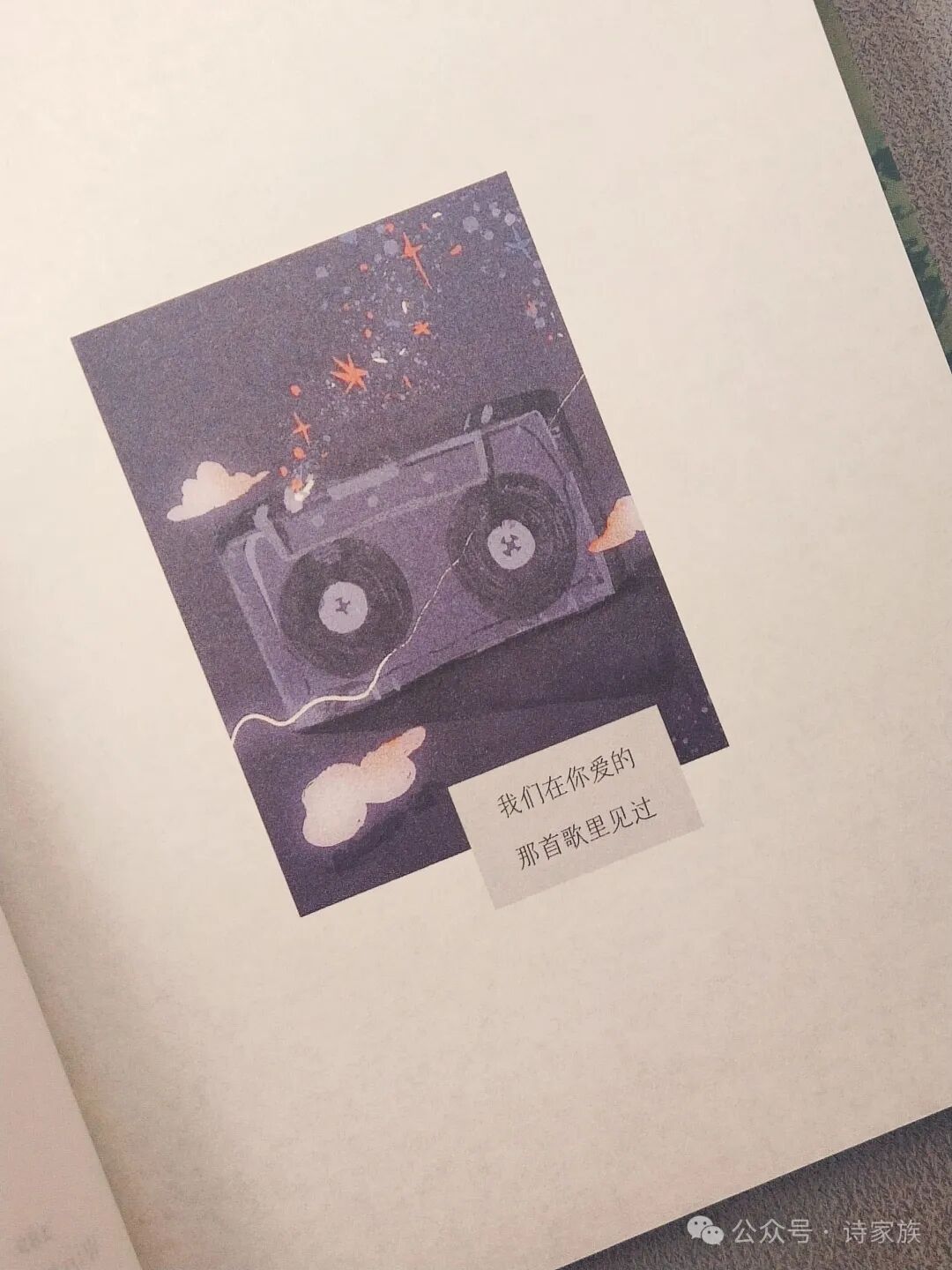
选择诗歌就是选择一种命运
——读卫国强史诗《到虞乡》札记
□叶延滨
卫国强的《到虞乡》作为一部精心构建的长篇史诗问世,本身就是一次庄严的宣告:诗人选择了以最厚重的诗歌形式,承载最深邃的命运叩问。阅读这部长诗,我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的成熟与风格确立,更是一次穿越历史迷雾、直面生存真相的精神壮游。
六年前初读其诗,我已预见一位心怀大爱的诗人正在崛起。彼时虽显青涩,但那份独特的感受力与对世界的赤诚关怀已灼灼可见。我在当时曾言:“一个诗人必须对这个世界有独特的感受,这种独特的感受引导诗人超凡脱俗地去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这种“诗意的发现和诗人的眼光”,在《到虞乡》这部史诗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恢弘与深邃的呈现。
卫国强这六年的生命历程,无疑经历了巨大的风浪与内心的淬炼。这种深刻的个体经验,被他升华为洞悉时代、叩问存在的哲学沉思,并最终凝结于“虞乡”这一极具张力的象征空间。“虞乡”,既是地理坐标——传说中舜帝德泽肇始的古老土地,承载着华夏文明“德孝”源头的荣光与理想;同时,它又是诗人脚下饱经沧桑、浸透汗泪的现实故乡。在这部史诗中,虞乡是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古老荣光与现代阵痛的交汇之地。它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个精神容器,盛放着诗人对故土最深沉的爱恋、最锐利的审视、最痛切的忧思,以及对理想家园不灭的向往。这部长诗,因此是诗人以生命为火把,在历史的长廊与精神的深渊中艰难跋涉的修行证言与命运交响。
在诗歌泛化、喧嚣的网络时代,《到虞乡》的诞生具有一种艺术史的自觉与重量。它是对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诗史”传统的深情回望与创造性接续,以史诗的宏大结构回应着时代的叩问:何为诗歌?诗人何为?《到虞乡》以其沉甸甸的体量和深邃的思考,给出了庄重的回答。
解读这部史诗的钥匙,无疑是其中那核心的篇章——关于“向死而生”的灵魂宣言:“波涛汹涌的大河/我的身体毫无指望的在向下沉沦/而灵魂/早已翻越身体的藩篱/浮出水面/在月夜/在虞乡/……/向死而生/只有脱去沉重的躯壳才能完成/灵魂向上的腾飞……/我死在虞乡炙热的夏天/将复活于诗歌/金色的秋天。”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突围之歌,更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在世俗的沉沦与毁灭中,唯有精神能实现超越与复活。卫国强将个体的苦难与救赎,置于“虞乡”这一兼具神圣光环与沉重现实的场域,使其具有了原型性的意义——虞乡,成为诗人与历史对话的圣地,也是其精神涅槃的祭坛。这种在肉身的消亡处寻求诗歌永恒价值的壮烈抉择,正是史诗精神的崇高内核。
诗歌,是中国人不朽的精神宗教。《到虞乡》正是卫国强作为当代“传薪者”,以生命体验书写的证词。我们这代诗人,是时代巨变的亲历者与记录者。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箴言,在《到虞乡》中得到了深刻而广阔的践行。这部史诗,是为时代留下的“真实的见证”,其视野从家族的血脉延伸到故乡的肌理,最终升华为民族百十年沧桑巨变的宏大叙事。
史诗中《家族简史》的篇章,堪称这种史诗性书写的典范:“小时家寒。爷爷说,从来就没吃饱过……/我的家族仿佛一条孱弱的河流/质朴,谦卑,疑惑不前/一直处于枯水期……/总是进了一步,又主动/退回三步……”卫国强以家族三代人的生存细节,勾勒出中国社会底层在历史洪流中的集体命运图谱。那“忧忧虑虑”、“颤颤惊惊”、“进了一步,又退回三步”的生存状态,精准地捕捉了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古老传统与现代冲击时的深层焦虑、坚韧挣扎与历史阵痛。这条“孱弱的河流”,既是家族命运的写照,也是乡土中国的缩影,更是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阶段曲折前行的隐喻。《到虞乡》这部史诗,以其宏阔的视角和深沉的笔触,成功地将个人史、家族史、地方史熔铸为一部饱含民族共同记忆的百年精神史诗,在个体命运的刻痕中折射出普遍而深刻的历史印痕。
史诗为时代立言,更为个体生命塑像,记录其荣辱浮沉。无论诗学主张如何纷纭,诗歌精神的本源、追求与底线永恒不变,即“诗缘情,诗言志,诗无邪”。《到虞乡》的磅礴力量,正源于其情感的真挚炽烈。如《出场》一诗,以“人生如戏”的隐喻,写尽个体在角色扮演中的挣扎、屈辱与对主体性的渴望:“为什么我不是齐天大圣,而只能/出演一个被他们算计/供他们驱使和鞭打的猴子?……/下次,我想,一定要赶在锣鼓敲响之前/走上舞台/独自蹦跶,上蹿下跳/美美地做回没有观众的主角……”三个“角色”境界的递进,揭示了人在社会规训中寻求精神自由的普遍困境,具有强烈的哲学思辨色彩和情感冲击力。诗歌无法许诺世俗的腾达,但能引领人“向善向上向美”,完成精神的自我修炼与救赎。卫国强在《到虞乡》中展现的,正是这种在困厄中重筑精神家园的坚定意志。
当诗人经历风霜,在《一掬汪汪的蓝》中坦然承认个体的渺小与局限,却坚守灵魂的纯净:“……为此,我不得不一再将自己的身躯/变小,再小,再再小……/小到成为海洋中一掬/汪汪的蓝。”这不仅是低调的自白,更是一种澄明的生命智慧,一种在浩瀚宇宙、无情历史和复杂的现实面前对自身位置的清醒认知,同时不失对纯粹精神价值的执着守护。这正印证了罗曼·罗兰所言的英雄主义——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卫国强的英雄主义,是诗人的英雄主义,是在《到虞乡》这部长篇史诗中完成的灵魂升华。
史诗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其思想的深度和情感的浓度,更在于其精湛的意象捕捉与细节的永恒定格。《到虞乡》中,《世间最重的一枚硬币》这样的篇章,将艰苦岁月中深沉的母爱,凝聚于一枚五分钱硬币的细节:“揣着白母鸡那枚温热的鸡蛋……换回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几十年过去了……在我心里/一直是尘世间/最重的一枚/它沉甸甸的,象座山。”
而《替那个时代羞愧难当》则通过孩童分享零食被批斗的微小事件,以小见大,折射出特定时代的荒谬与压抑。这些岁月的珍珠,被诗人精心打磨,镶嵌在史诗的宏大叙事中,成为支撑诗意的坚实支点,也是历史最鲜活而疼痛的注脚。史诗非小说,它不依赖虚构的情节,而是依靠真情实感和典型细节的震撼力直击人心。卫国强以这些源自虞乡土地、饱含生命体温的细节,构建了史诗坚实的地基。
我在六年前称卫国强为“有大爱的诗人”。《到虞乡》这部史诗,更是其大爱的丰碑与解剖刀。生于虞乡、长于虞乡的诗人,其爱的根系深扎于这片交织着荣耀与苦难、美好与丑陋的土地。史诗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人类心灵的永恒伴侣,核心在于它培育、守护并传递着普世之爱,这种爱,不回避它的苦痛与阴影。卫国强在《到虞乡》中深情书写父母之爱,视之为“人世的太阳”。尤为震撼的是《遗言》中对母亲临终话语的记述:“低低地,疲惫地说: 你们不要难过 /人到这世上,就是吃苦来了/ 苦难吃完了/也就……该……走了……//听后惊异 /母亲这话 该是由佛来说的呀!”这朴素的生死观,蕴含着宗教般的彻悟与大地般的慈悲。它教会我们在认清世界(包括虞乡)的不完美甚至丑陋后,依然去深沉地爱这个世界。卫国强的史诗,正是这种深刻、包容、坚韧的大爱的传递与升华。面对当下诗坛某些浊流,《到虞乡》以其光明与深沉的爱,守护了诗歌“思无邪”的神圣底线。
诗歌创作若仅止于语言技艺,终成无魂的躯壳。与早期作品相比,《到虞乡》展现的卫国强,其内心世界更为通透、开阔、深邃,也更能包容现实的复杂性。这部长诗本身就是诗人与诗歌达成的生命契约,是与读者进行的灵魂对话。史诗中《清除我》一章,是彻底的灵魂自白:“就我,就现在,想清除掉身上/那些多余的东西……/只要能将我酿成的那几行沉甸甸的/诗句,留下来,这就够了/百年风雨后,阳光下/它们依然会金子般/兀自生辉。”这是一种精神涅槃后的澄明境界。佛家的“断舍离”,圣贤的“舍得”,名士的“放下”,其精髓皆在于此——在尘世的喧嚣、诱惑与现实的浑浊中,保持内心的淡泊与澄澈,将生命最终的价值锚定于精神创造(诗歌)的永恒光辉。《到虞乡》这部史诗,正是卫国强践行此道的庄严结晶。如他在《大地慈祥》中所悟:“大地慈祥,它总能/用物的暗喻,给人以/微茫的信心。” 优秀的史诗诗人,正是这慈祥(亦可能严酷)大地的赤子,以诗行播撒在认清现实后依然不灭的信心与力量。
《到虞乡》的问世,标志着诗人卫国强创作历程中的一次伟大飞跃与精神标高。这部作品以其厚重的历史感、深邃的哲学思辨、真挚而复杂的情感力量(包含对故土美与丑的深刻体认)和精湛的艺术表现,构筑了一座精神的殿堂。它既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家族奋斗史,也是一幅饱含挚爱与批判的故乡风情画,更是一部浓缩了民族百年精神历程的恢弘史诗。
我深信,《到虞乡》将以其独特的价值在中国当代诗歌艺术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它证明了在浮躁的时代,依然有诗人选择以诗歌为命运,以史诗为担当,为时代立心,为生民立命,为脚下这片交织着舜帝德辉与百年风雨的土地,唱出最深沉的歌。
祝贺卫国强史诗《到虞乡》的诞生!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里程碑,也是当代诗歌的重要收获。借用诗人史诗中那充满希望与力量的句子作为祝福,也献给所有热爱诗歌、相信精神力量的朋友们:“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它通体都是金黄的色彩,金黄的希望,金黄的喜悦/我重新迈开双腿,我就要自由自在的行走了/我将重新丈量脚下这块古老的大地……”愿《到虞乡》这部史诗,成为我们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古老而复杂的大地,思考民族命运,丈量精神家园的永恒坐标。

(叶延滨,当代著名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原主任,《诗刊》原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