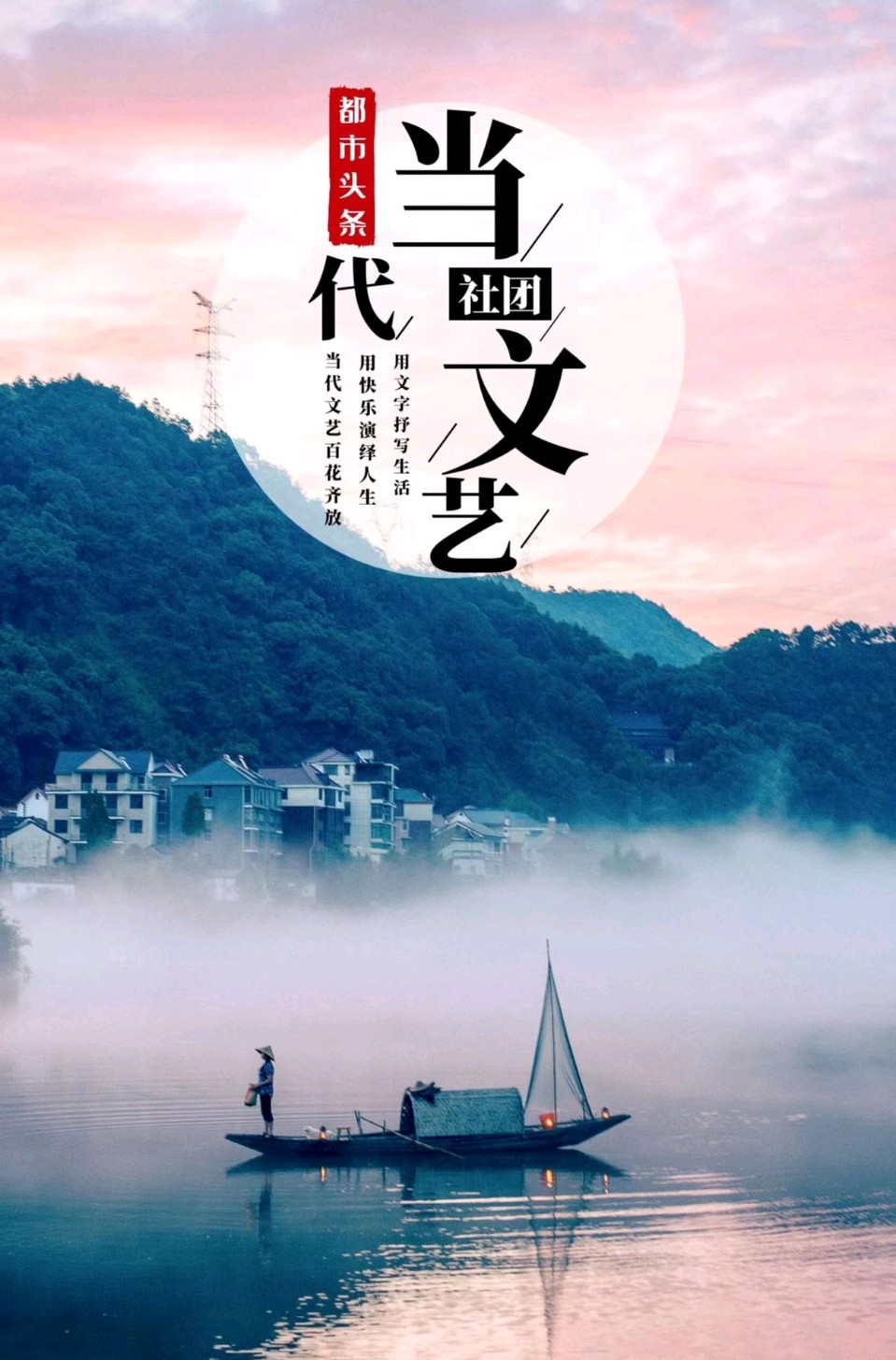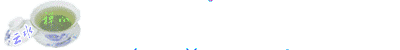臭鱼庄的草窠里飞出了金凤凰
作者:王玉权
三阳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而开凿的人工运河古邗沟。南北走向的古邗沟历史比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还古老。这条河古名三阳渎,流经古镇三垛后向北的一段由于年久失修,河底淤积,河堤残缺。尤其是东堤,河滩被蚕食垫高砌成民居。最窄处仅存几米,河心处虽可通航,但行洪能力已大大受阻。三阳河已苍老不堪,面临断航之虞。
那时,三垛一带叫三垛人民公社,北面草荡一带叫司徒人民公社。夹在中间的,便借用三阳河名为三阳人民公社。
三阳公社设在行政范围适中的臭鱼庄。庄上人家绝大部分住在三阳河西,河东仅有三五户人家。这地方正经叫北俞庄。其所以有这难听的穷名是有来历的。它和团转村庄不同,人家好歹都有一条或几条砖街,房屋依街巷排列,基本整齐。这儿却像个乱葬岗,大小高矮不等的房子不上家数,犬牙交错地乱搭乱建,没一条较整齐的街巷。人走进去像进入了迷魂阵,半天绕不出来。
从三阳河里上来的渔民,七拐八拐地在庄上兜转了半天,一篮小鱼一条也未卖出去。这里人家太穷了,经常揭不开锅。大太阳当头了,许多人家烟囱里不见炊烟。小鱼经不起大热天几个时辰闷焐都发臭了,只好倒进茅缸。距北俞庄不远,南有南俞庄,东有东俞庄,偏偏北俞庄不争气,普遍穷得要死。俞、鱼谐音,卖鱼人仰天长叹,咒骂这儿是个臭鱼庄!
好名不出庄,臭名扬天下。臭鱼庄的穷名便传扬开了。
臭鱼庄成了公社所在地,通庄找不出一处可征用来作临时办公的处所,只好在三阳河西空地上搭建临时棚屋办公,是名副其实的芦蓆公社。
公社在三阳河东划了一大块地创办三阳中学,和公社办公草棚隔河相望。这里仅有腾空了的十来间泥草房,外墙全系夯土垒成的,上面大大小小的孔洞肉眼可见。大概不是鼠洞便是蛇窝了。此外便是留有稻茬的农田。
公社化后的农村有个口号,“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片,高中不出社。”三阳中学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这块地东接一望无际的大田,西临三阳河;南隔小河是几十亩大小的独圩口成了粮站;北隔东西向的大路是供销社棉花收购站、仓储、职工宿舍。
一南一北两家均是当年炙手可热的豪门,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人家有钱有势,正在热火朝天地大兴土木。夹在中间的三阳中学像个落魄的瘪三,冷冷清清,可怜兮兮。囊中羞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因陋就简,利用破泥草房作办公室、教室。砌了两间斗拱砖墙的食堂。用芦材箔两面糊上泥巴,隔了几间斗室作教师宿舍。我就在这芦材墙芦材门的矮草棚中住了好些年。
两座草房中间米把宽的过道也利用起来,封上顶,开个门,就成了总务处会计室。
那时无自来水。炊工每天总要从三阳河中挑几十担水倒入食堂水泥池中澄清以供食用。特别是冰雪天,码头上冷风飕飕一跐一滑的,十分辛苦。
那时也没有通电。办公用煤油罩子灯,学生晚自习用汽灯。下晚自习后,许多同学开夜车,自备用墨水瓶制成的油老鼠。油烟把两个鼻孔熏得黑糊糊的,有的女生甚至长了“胡子”。同学们常以此互开玩笑,苦中作乐。
平整下稻茬田,竖起篮球架,立根旗杆,挖个坑,跟人家要些黄砂子,就成了跳远坑。这些算是学校特有的标志。
一无校牌,没处挂,土墙矮,还没牌子高呢。可能有过吧,厚木板被人搁到码头上作了跳板,倒派上了用场。
二无围墙,讲究不起。外观上人们看不出这儿是堂堂中学,和极普通的农家厍子没区别。
临河有一条煤渣石子路,那是南面粮站铺的通向大桥的路,我们沾了大户的光。阴雨天过桥去河西供销社,免了泥泞之苦。
那时的三阳河桥,吓人呢,想起来犹然心有余悸。杨树段子作桥桩,杨木板子铺桥面,长长的五搭。为了行船方便,桥呈拱形,拱形中心像飘在空中。我虽生在水乡却是个旱鸭子,胆子小恐高恐水。每行至中央,腿便吓得摇摇的,身不由己地蹲下,继而俯身学狗爬,出尽洋相。佩服小朋友们像细猴子样灵活,且故弄惊险动作的矫健灵巧。
校园里空地倒是不少,也有零零星星的寻常树木,就是没人规划种些花草美化一下,没心绪。留作砌教室的地方成了撂荒的田,杂草的窝。
打通现有的三间农家泥草房,土墙上挂块黑板,搁几张人家淘汰下来的学桌凳(那是校领导费了多少口舌跟城上大学校作揖化缘弄回,请木匠简单加固后重新利用的弃物。)就成了教室。穷单位的穷办法,犹农家“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耷耷给老三”一样,蒙混着过日子。
世上有三无产品。草创的三阳中学,天晓得有多少个“无”。三无产品是假货,三阳中学即使有再多的无,也是货真价实的正牌货。
单讲我们高一班吧。1977年秋,三阳中学招了个五十人的高一班。恢复高考的春风如久旱甘霖浇开了人们的心花,似祝融之火燃爆了神州大地。昔日门可罗雀的清水校门,一下子成了疯抢的香饽饽。除了正取生,还有复读生,凭借各种关系安插进来的插班生。那辰光走后门之风大炽。这个书记官、那个什么长、这个支书、那个小舅子,校长头都大了,一个个都是爷,得罪不起。外要应付各种社会关系,内要饱受学校老师的抱怨炮轰,里外不是人,自怨自艾戴这顶破乌纱活受穷罪。结果五十人的班涌进了七十多人。没办法,双人课桌三个人挤着坐。为了腾地方,讲台撤了。坐前排的则需要仰起脸才能看到黑板上的字,坐边上的干脆看不到了。坐后排的埋怨前面人挡了视线,需要站起来看。乱糟糟的,学生也喊活受罪。
面对内外夹攻,徐校长成了受气包。我心柔软,常劝同事们少给点气他受。人家却说,这破学校样样都抓不上手,他还尽说漂亮话。我们又不是三岁伢子,好哄。他徐大话既是一校之长,不找他找鬼啊!
“徐大话”是我们送给他的绰号。他是个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事无巨细一把抓,成天忙得要死。又是个唱高调的教条主义者,满嘴的政治正确。什么继承主席遗志,继续革命立新功啦;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共产主义培育接班人啦;纲举目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要泄气,面包会有的啦……马列主义大道理不离口。乱开口子,许诺总总难以兑现的诺言。我们这班人中,大部分都是民办教师。他总用“转正”来吊我们胃口,好像他有天大权力似的,把我们当三岁伢子哄,太可笑了。老师们背后都讥讽他吹牛屄、放空炮、大话疗天。
徐校长,三垛人。国字脸、黑皮子、瘦寡寡的大个子。城市贫民出身,初师文化程度。知识分子圈里少有的“布尔什维克”。肚里墨水不多,去教书大概没甚名堂,当校长倒是块料。这人最大长处是没官架子,平易近人,任劳任怨。尽管天天吃瘪,不记仇不记恨,从不给人小鞋穿。和他好许愿一样,那些不着调的话都是易破灭的肥皂泡。
近二十年的小学初中教学,悟出了教学的唯一核心,即传统的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训练。其它动听的名目均是花哨的外衣。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正确诠释了熟能生巧,知识量和技能之间的关系。读得滚瓜烂熟,具有足够的数量,然后才有可能转化为技能、能力。
语文的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就是双基训练由浅入深由简入繁的渐进过程。凡离开双基训练的课均不是好课。每见有人在公开课上借题发挥以显示个人才华,我认为那是哗众取宠的废话,无用功。
有些朋友六七十岁了,诗文中仍不时有错别子,别扭的句子,不通顺的篇章,病根就是当学生时双基不牢,一生受累。双基训练的真功夫如同滴水穿石。看似轻飘飘的水滴,一旦专一,久久为功,必收水滴石穿之奇效。这就靠教师的盘功。“盘”,形象生动,功到自然成,生的盘成了熟的。有人懒得去盘,做天和尚撞天钟,一教了事。这种教师就是不合格不负责任误人子弟的浑虫!
在南濠,我有个高中毕业当代课教师的小同事陈学书。他有意参加77年高考,要我帮他复习语文。翻看他四个学期四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发现不少课文都是我以前学过的。当年,我们学的是汉语和文学两本书。汉语主要学语法,文学书中古文言文分量较重。我把他的四本语文书一一列出知识点。运用写作知识写好记叙议论说明三种文体。根据我的判断,押注刚恢复高考的作文大概率为记叙文。也根据初中作文大致规律。教他牢记“写一人,二三事”“记一事,全过程”(略头尾,详中间)的诀窍。至于什么凤头、猪肚、豹尾,注意就好,不作过高要求,重在文通字顺。时间紧迫,只可雪中送炭,难以锦上添花。经百十天训练,就匆匆上阵了。总分不理想,仅二百多分,但语文就考了68分。我还是很欣慰的,作文体裁押得不错,知识点抓得也对。人家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望眼欲穿不见鸿雁。他自知沒戏了。小青年有志气,表示不灰心,来年再考。哪晓得77年12月底了,无锡轻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方姗姗来迟。天上突然掉馅饼,欢喜得小陈疯魔了一般,先是双拳紧握激动得跪在地上狂呼乱吼,继而躺在地上直打滚。新上身的大衣沾上了一滩臭狗屎。老师们都哄笑着,说他交了狗屎运。
小陈的录取,让我心里有了底。谢师宴上,我对徐校长说,我非孔明,难为你三顾茅庐(三者,多数也,非确指)。(其实,他不知颠了多少趟了。)敢借《出师表》两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接手这块烫手山芋。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三个学期后的79年高考,很可能剃光头吃鸭蛋,那可不能怪我。徐校长一听,喜笑颜开。双手作揖,连呼阿弥陀佛,不怪不怪不怪。
我又特别强调,要我教语文当班主任可以,但你们应当放权,让我们拼命一搏,不许行政干涉我们的教学业务。徐校长拍胸脯,不干涉不干涉,这个班就交给你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气,要么不答应,一旦答应了的事,绝对不会虎头蛇尾,务必善始善终。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非常崇尚古君子之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这人像条牛,一生就做一件事一一教书。像牛犁田一样,几十年不厌其烦做着重复的劳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性子也像牛,认准了的,八条牛也拉不回。说我犟,固执,顽固,“无如臣脑固如冰”,听便。牛,皮糙肉厚不怕打,倒是打牛的家伙手打疼了,憋了一肚子气。哪怕大卵子气得胀下来了,关我何事,活该!一生如牛负重,敢说成亊有余,从未懈怠败事。奔九的人了,不说瞎话,否则,对不住良心和年齿。
1978年春,我中途接手了这个班。已然浪费了一个学期,仅剩下三个学期就要参加79年高考了。我们这班歪嘴和尚,在我的带领下,抱成团,摒弃一切冗余,把所有精力花在必考的几门课上。以双基训练为核心,大水漫灌,严格考核。时间金贵,来不及细水滴灌,慢滋侵润,只好狠心把刷下的编入文科班。寄希望以理科班,对拔尖生开小灶,重点培养。舍卒保车,随高考指挥棒转。那可是国家抡起的大棒,随之起舞大方向不会错!
我的铁腕治理引来不少非议。我们一班人顶住压力不为所动。学校领导承守诺言不干涉,可谓“开明君主”。他们只愿不出纰漏平安送走这届细猴子,这个班太让他们操心了。
细猴仔们好哄。冲出农门的诱惑足以让这班淳朴的农家子弟钻入书山沉入题海之中奋斗不止,无怨无悔。目标明确,飞跃龙门,折桂蟾宫。不用太多的煽情,教与学,双方均上了轨道,渐入佳境。
龟兔赛跑的寓言足证笨鸟先飞的真谛。莲花出汚泥而不染,硕果付辛劳才甘甜。那一年多,光经我手,钢板就刻坏了十几块,汽灯纱罩用去了几十打。
1979年初,全县数理化竞赛。我班夺得了化学第一,数学第二,物理第二的优异成绩。令全县中学大吃一惊,从此名不见经传的三阳中学被人刮目相看,纷至沓来参观取经。没什么可观的,也没什么经,就一条筋,勤和苦。
数月后的79年高考,1400多万的考生争那三十五万名额,竞争惨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我班近40人参考。出乎意料,不但没有剃光头,居然有二人上了重点大学。高中中专前三甲及一个第十名均出自我班。前前后后,让十几名农家子弟飞出农门改变命运,捧上了令人艳羡的铁饭碗、金饭碗。
臭鱼庄的草窠里飞出了金凤凰!
几十年后,79届高中同学聚会时,母校三阳中学已彻底消失,了无踪影。原址成了安大高等级公路的一部分。车轮滚滚,重卡穿梭,日夜呼啸,异常繁忙。宽阔的路道两旁,左右两边的钢护栏似两道银色的飘带飘向远方。护栏外四季常青的花木,似斑斓的花边镶嵌在银栏外延展到天边。
整治后的三阳河涅槃重生今非昔比。拓宽了的河面上浪激流湍滚滚北上,南水北调东线重点工程,尽显国家级大手笔的凛凛威风煌煌气派。粼粼波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晃得人睁不开眼,浪花在峥嵘的护坡石上撞击出梨花万点,形成的濛濛水雾如梦似幻。
两岸留有几十米宽的护坡林带,高大的乔木犹两条绿色长龙夹护着这条通向京畿的生命之河。
气魄宏大的三阳河大桥如长虹卧波,两辆汽车可以并排通过。过桥向东二三里,便是北宋一代词宗秦少游故里一一秦家垛。
昔日的臭鱼庄已变身别墅楼房鳞次栉比,花木扶疏香袭四季的三阳社区。
山河依旧,面目全非,旧貌变新颜。恍如隔世,换了人间,欣逢新时代!
【作者简介】
王玉权,笔名肃月。江苏高邮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而不休,码字怡情。不钓名和利,只钓明月和清风。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