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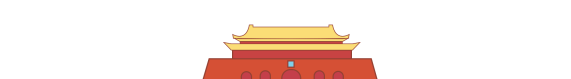

目送
文/浔衷
“这道附加题,有人答得出来吗,我点名了啊,咱们班谁叫——”
后排窗边一个梳高马尾的女生站起来,手里还拿着扇风用的练习册,没抬头看我。深蓝色的窗帘遮不住盛夏,像握着一层薄薄的珐琅,抹在她的刘海上,又偷偷从她发隙间穿过。
她不抬头看我,我反而有些心虚。偷偷瞟了一眼讲台上手机里她朋友圈的自拍。那是她和她妈妈被迫共用的微信号,专门用来加班级群的。不知为何,半年前的动态里,还留着她和班里同学过生日时去海边玩的照片。
老师,你点她干嘛?我们班其他老师都不叫她回答问题的。下课后,前排戴眼镜的男生开玩笑般告诉我。
升旗仪式时我在教室准备下节要用的试卷。走廊喧嚷之后,只剩她独自在教室。六十个座位上蓝色桌板连成一片深海,一摞摞课本和练习册在其上浮沉。她趴在海平面看书,蓝白色校服像浅海的一卷波浪;这是学期过半的日子。粉笔槽的灰被阳光照得看不见,窗外是远处火车驶过的声音。
后来我在海边向她提起那一天的时候,她告诉我其实她早就做好了被叫起来的准备,只是没想到那么快。我只好慌忙说自己也是一时冲动罢了。她没看我。灰蒙蒙的天将海水和沉沙裹挟到地平线对岸,站在沙滩上的她却好像被遗忘了。必然是天空也冷得困倦了;这又是十月底。海边的游乐场空无一人,连售票的窗口都关了。这里像是被隔绝的一处村落;或是一片净土。
我们放了学才来到这里。上自习的时候,她悄悄溜到办公室。我一抬头就看到她笑着看我。手里还拿着一袋东西,像是找我有什么事情。但看到屋里还有其他人,她又转头走了。放学后我在电动车后座上仰头问她,你下午找我来是做什么?她把书包塞到我手里。电动车穿过小巷和商铺,拐了好几条街。我拉开书包找起今天留的课上作业。果然,她还没写。课上的题你怎么都没写?我又仰头问她。她右边的耳朵有一个小小的耳洞,今天才发现。
我买了点零食想给你吃!你还没尝过我们这里的特产吧。她完全没答我的话,也还是没回头看我。红绿灯迎着海风,吹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抓起左右摆的马尾放到卫衣帽子里,侧过身想看清她的表情。
越靠近海边风越大,电动车翻过斜坡,发出尖细的电机声。过桥洞时她大声喊,看什么看!多危险啊!罚你把课本抄一遍。说完自己就大声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个不停,却不敢松开抓住她校服的手,担心一不留神就被甩出去。
她一步步走向海边。海水与湛青碧绿都相去甚远;是明显被污染了却又混着清新腥气的颜色。她的背影,在天地间成了小小一粒,像只落单的孤雁,蓝白相间的校服成了最纯粹而又最孤寂的点缀。天空的颜色在此时也显得含混,介乎浅蓝和浅粉间的调和。方才路上的热闹,好似被海水吞没般不见踪影。她停驻许久,像在眺望更远处明灭的渔火,又像在细数逶迤卷来的浪。海风吹得脸湿漉漉的。她扭头对我说,回家吧!我妈妈不让我待太久!说着就往回走。
我没反应过来。以为她还在海边的时候,她已经跑到我眼前了。傻啦?她在我眼前挥挥手,然后手缩到校服袖子里,用袖子牵住了我。我低头看了看她,她也侧过脑袋瞟了我一眼。
这么冷的吗?她没回答我。我又坐上了电动车的后座,回身向大海望去。十月的海水容不下过路人,却无比温柔地抱紧深秋和过往。奶奶让她回老家读书,但是她母亲却坚持让她留在城市里。离高考还有整整一年。
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辞职的前一天。学校操场后一大片桦树林间,是横贯着的火车道。我和她面对面坐在操场看台,长长的列车从身侧轰鸣驶过。天色渐晚,我催她赶紧回家。她告诉我,奶奶来了,不想回家。绿皮火车上镶嵌着的车窗光亮,连成一条斑驳的线,在桦树林间奔行着,画出一道稍纵即逝的银河。她又说了一句话,我恰好没听到——她的父亲去年出海后,就再也没能回来。我后来的后来想,我也许不该带她去海边。
火车在我们的注目礼下消逝在黄昏里。她挽了一下刘海,低头若有所思。我望着天,随口讲着以后的计划,同学们的八卦,还有这季节和火车。哎,老师。对面的女孩子叫了我一声。她把手缩到校服袖里,用手撑开袖口递给我。我知道我抓住校服,打上了结,对着她嘻嘻地笑。仿佛下了决心似的,她晃晃被我系扣的胳膊说,拜拜。你该走了。说完,她从兜里掏出耳钉扎在耳垂上。
终于还是上了火车。面对着即将而来的风景,我原以为我有一番心情去遐想和追念;但我如来时一样,仍是沉沉地睡去了。我知道我离海越来越远。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她的未来甚至今晚,又会与谁相干呢。
车窗亮起了灯,穿过一片桦树林,又被拉进了望不尽的旷野。

作者简介:
浔衷,1999年生,河南新乡人。语文教师,文学硕士。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截稿日期:2025年3月31日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