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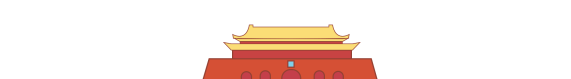

轻唱陌生的歌
文/何杨璇
前几天,朋友请我到大剧院看了一场戏。那是昆曲。很奇异的体验,我第一次在公开的大场里听戏。演员眼神顾盼,似星雨流转;手指翘起,似蝶翼微微颤抖。我清楚地看见,他们胭脂水粉下难以掩盖的红晕和虚汗。我深深同演员一齐共事历情。所以感知被无限放大,听曲时也留心许多异感。演员唱曲,戏词会随着情感需要,而延宕吐字或曲折语调。在气息游离和丝连的间隔中,我听到了某种哀怨。最为古雅的昆曲尤特别。《墙头马上》中裴尚书吩咐下人做事,仅仅是这一不需要过激情绪的日常语气,都可以听到声音中拉伸的幽哀。突然惊醒,这种熟悉我经常在噩梦里听到。
每逢大院有人去世,我们家都出席丧礼。因为大家全然互相认识,生活于这种邻里集合体,窗户没有不透风的,婚丧嫁娶的密信也构成另一种亲缘纽带。我从小就熟悉葬礼上的唢呐和锣鼓声。人刚死,头夜和第二晚总要敲打到两、三点半钟。夸夸拉拉,嚓嚓铛铛……铜锣的惨叫,伴随道公浑糊而焦急的念经声,或是家谱或是超度死者的颂文。我又以为是在唱歌,因为永远听不清字词。语调或紧到嗓子,或拉长脖子;声音混浊而催逼。听到往往会做噩梦,我不敢睁眼,疑心看到魔鬼。天明时,我躺着看窗帘上的黑褐色图案,恍惚见到人走到黄泉前喃喃自语。
我轻踏过石板路,穿过忙碌忘我的人群,他们看我像看陌生人。我无所事事;她们收拾碗筷,淘洗蔬菜、猪羊肉;他们上大锅,尽力翻炒里面的一滩菜汤和肉。男女们在闲聊,嗑瓜子,烤火,烧橘子皮,不转头看我。让我烤吃橘子也是坐不住的,于是脚故意陷入泥土里,撑着起身,走到房子的后院。我抬头看见,正门上方盛放的空旷,原来这里是有一口棺材。我耳边轻轻响起几年前的对话。堂哥领我看这个太姥,他说这个棺材是她早就预备好的。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习惯,不然到时候来不及准备。我那时不敢问,这样是否太过悲观。要是大家都不这样做,或许可以用来不及准备的棺椁去假慰自己尚处康健。现在想来,那时我还是太年轻,不知人世无常。太姥的棺材,从门上移到地上,最后放在土坑里。这当然是我臆想,最后的场景是我看不了的,我没办法继续跟着下葬人群,我不是血亲。
我的爷爷最先离世,接着是奶奶,前年外公过世。
爷爷死的时候我五天不许吃肉。大伯说不允许。但是大嫂说可以偷偷吃,姑姑也说偷偷吃,爸爸却说你还是别吃了。好像是第三天,我睡在厅堂,旁边睡着棺木,里面睡着爷爷。我被吵醒。一阵一阵的脚步,又近又远,窸窸窣窣的人群。我好像掉进了噩梦里,然后被爸爸拉起来,跟着亲戚们,围着厅堂正中躺着的爷爷,转圈圈。妈妈在圈外,递给我一柱香,胡乱给我套上一顶白巾搭的尖帽。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转圈,爸爸说她不想也不用。我还是吃肉了,跟着村里其他小孩一桌,远离着大人的。姑姑看到我的空碗有油,问我你吃肉了吧。我说对啊我吃了。姑姑笑了。后来搬棺木上山的记忆很模糊了。我只是循着铜锣声在走。我只记得奶奶、姑姑和爸爸哭得很伤心,我没有哭。我只是想起了我六岁的时候,我递给爷爷一颗糖,他接过去没有吃,我隐隐不高兴。但听到爸爸偶然说爷爷已经不能再吃糖了,我感到惊讶而难过,因为我小时候觉得不能吃糖是一种人生惩罚,生活会因此变苦涩很多。
奶奶死了,爸爸哭得比爷爷去世那天还要痛苦,脸皮皱在一起,中年的皱纹盈满泪水。这时候,我已经拥有比过去更清楚的意识了。我也感到非常伤心。我这次五天没有吃肉,发自本心不想吃,尽管我那几天常常因为缺油水而半夜饿肚醒来。姑姑也不再劝我吃。我们都去送奶奶上山,在远离爷爷十二公里的老屋后山。那儿很近,方便我们常去看她。爷爷离开得过早了,地皮选的是他曾牧过牛的偏田边。那已被时间冲刷了一遍又一遍,那段岁月,爷爷对儿女们讲述过的故事,或许都已在记忆中添油加醋。他的童年面目全非,就连成人的印象,在我也仅是模糊背影,连我的记忆也更偏好记住奶奶。
老屋的后山雾气缭绕,上山的石路面上格外多枯枝败叶,路旁几排黑松林,针叶上挂着昨晚哭过的泪柱。跪在很厚重的土堆前,点的香很熏眼,我熏得眼黑淌水。冲天的鞭炮打在心里。空中的炸亮里,我看到奶奶躺在病床上,周围很多我不认识的亲戚。大伯拔开白酒塞,撒酒到地面和碗里。我看到奶奶坐在庭院里,穿着米黄色的毛衣,我睡在她的腿上。送葬大部队浩浩汤汤地离开后山,我落在最后,转头瞟了一眼被老屋挡住的坟墓。我看到奶奶虚掩的门缝透出的一丝暖光,那是我回城里的最后一眼,那是我上高中前最后一个假期,之后内宿就很少回家。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从回忆奶奶之初立马能想到,却在改此文的最后一次才加上。爸爸在哭奶奶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以后再也没有妈妈了。这确实是一句平常的话。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像是你在看那类催泪情节中需要被规避掉的庸常文字。这是在做文学技艺中不加修饰的情感,是很白的东西。然而我当时被这句话迎面击中,过去的心里瞬间长出了几百只手掌,试图抓住未来的我的失落。
外公去世,妈妈比我前两次经历里哭的人还要悲切。妈妈的哭声是羊跪乳而泣涕。那几天天气很冷,我穿羽绒也感受到家里仿佛一个冰窟。村寨里的人倒是没有太多悲戚,只是冷静的脸面。我高中毕业第一个暑假,那几个村口的老人,有几个不见了。死亡渐渐平常而淡漠,大家还要生活下去。我第一次清楚地参与一种灵魂摆渡的方式。天蒙蒙亮,我和妈妈还有表亲们,双手高举白绫,排成一条虫。我在倒数第二个,背后是外公的妹妹,也就是姑姥。白虫踏过泥泞,穿过稀疏的车流,钻下桥洞,到达河边的缺口。缺口有一个小台阶,可以直通水底。旁边有一个长满青苔的古黄的水车,已经不再转动。表姨说这就是道公说的风水宝地了。我们照例跪缺口,叩拜,点香,倒酒。大家哭过到这就不再哭了。姑姥临走时念了一串咒语,我感到熟悉,应该是道公念过的,但已经不再是噩梦。我见到了清梦里,那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已故老人排着队,一个个走上一座黑色的桥,喝过水,怀着微笑过桥。
我不大了解传统观念和文化。对比瞬息多变的世界,它们仿佛停在原地,我无暇融入它们。后来我上民俗课,看《滚拉拉的枪》。滚拉拉跟师傅学指路歌,起初不解,但后来滚拉拉给猝死好友贾古旺唱歌使其灵魂归所,我泪流满面。我突然想把记忆捡起来,好好问问过去的老人:丧礼上,道公唱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唱?唱的内容都一样吗?很遗憾,我已经过了可以假借无知,去问出天真问题的年龄。对已逝之人的故事和那些传统的事务,我知之甚少,懵懂时觉得如噩梦般,不敢靠近的心情断送了一种与之联结的可能性。现在只能缝缝补补,轻轻唱起陌生的指路歌。

作者简介:
何杨璇,女,壮族,21岁,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爱好纸质书、躺平和跑步。文学创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会坚持写作。
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
furongguowenhui@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我们尊重您的每一次来稿,承诺每稿必复。
《品诗》公众号:readpoems520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
为期一年,入选作品会择优按顺序在大赛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大赛作品集。
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九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2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微小说多篇(每篇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参赛限投一次作品,请您挑选您的最满意作品参赛。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入围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依等次颁发相应获奖证书,镌刻名字的奖杯和奖牌,获得者将获得高档英德红茶套装。
赞助商:
英红九号!中国三大红茶之一,温性红茶,浓郁芳香的甘蔗甜醇香,口感浓爽甘醇,满口甘蔗甜醇香持久不散,茶客最爱!欢迎广大朋友联系咨询:吴生18819085090(微信同号)诚邀更多赞助单位赞助本大赛,有意者可以邮箱联系。
自费出版事宜:
如有书籍出版意愿(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等作品集)
出版方式为国内书号,国际书号,内部出版,任选其一。
请将您的书稿及联系方式投稿至
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文学翻译征稿启事:
如您有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等文学作品集或者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需要翻译,您可以投稿到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专业文学翻译,价格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