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母亲二题
文/刘志平
养母
我比别人幸福,我有两个母亲。
我的出生并非是一件让家人高兴的事,在我之前我已有四哥一姐,多了一张嘴,添了母亲的愁。所好母亲的干妹妹喜孜孜地要了我,她没孩子,就这样我成了人家的养子。母亲说我是糠箩里跳进米缸里了。
养母对我很好,疼我,痛我,当作亲生的儿子,只差没在自已肚子里怀上十个月。
养母人生得很俊,两条弯弯细细的眉毛,很秀气,文文雅雅,说话柔声柔气的,没高声,很有教养。
养母不象别人家怕养大了儿子又飞走,我天天往生母家跑,她从不拦我。养母欢喜我,不放在脸上,怕宠坏了我,成不了人,长大了没出息。我不听话,惹了祸,她照样指责我,但从不打我,骂我。错闹大了,才告诉我生母。生母性子暴,一发火,就会用那皮实坚硬的藤拍子抽我屁股,疼上好几天。
由此我总愿意听养母的调教,而不想去生母那儿找揍。更谈不上去生母那儿撒娇卖嗲,生母养了那么多伢儿够烦了。我在养母家小日子过得很惬意。
养母在饭店当售货员,每天早上在店里卖早点。找零钱的铅币放在票箱边上的一个小瓷碗里,那铅币曾经强烈地诱惑了我,让我的馋嘴很恣意地享受了一番。被养母发现后,从未打过我的养母,居然用一根宽宽的皮带抽我,平生仅打我一次的养母,使我受到一生中最深刻的教训。那次惩罚的效果很好,让我成了一个虽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人,但却成长为一个遵章守纪品德良好的公民。
养母生于镇上一个旧式人家,知书达理,对有学问的人很敬重。养母对我寄于厚望,想让我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平日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当然我没给她失望,每次考试都得高分,每个学年是三好学生,年终老师评语都是赞誉。每每这时,养母舒展舒展的眉儿更好看
文革开始,我失去了继续求学的资格,大约是养母喂养我的这米缸有点“霉菌”。养母家社会关系有点复杂,政治不清白,不可能把我喂养成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我也就不能继续求学而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了。养母的希望落了空,眉儿皱得紧紧的。
1978年后,人们的日子过好了,养母眉儿展展的,很开心。可她病重了,气喘吁吁的,一到冬天,人喘得象破风箱,久之久之,转为肺癌。大家瞒着她,其实养母心里知道,她晓得大家的心意。也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是独自一人暗暗地啜泪,一来人又满脸笑。
生母送来了很多可口美味的食品,还有一支陈年的老参,养母看着这么多的东西,已是咽不下,只是两眼直直地瞅着生母,瞅得生母心里直发寒,养母有话对她说。
话是非说不可了,养母拉着生母的手不放松,气喘吁吁地说,姐,我对不起你,没把平儿拉扯大成个家,连家具也没置一套,我只想给孩子打张床,让我看看,也心安……。
当晚请来了木匠,吃了开工酒,养母很高兴,吃了一碗粥,说了很多话,夜里,养母长叹一口气,走了。
等我结婚后,睡在那张红漆堂堂的床上,总想起我的养母,含着泪和妻说起我的养母,要是养母能活到今天,该多好。
我有两个母亲,很幸福,又很不幸。
桂姨
桂姨是母亲的干妹妹。
咱两家住紧壁邻居,仅隔一板壁,说话都不要过门。我母亲长得高大粗壮,嗓门大,脾气暴,好打抱不平。桂姨生得赢弱,单巧苗条,有着江南女子的秀丽,说话柔声柔气的,对人很和善。
两人的外型和性格反差很大,但没妨碍她俩成为一对最要好的姐妹。
母亲身体好,善生养,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的兄弟姐妹接二连三地来到这个世上。桂姨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特别喜欢我们兄弟姐妹。
桂姨家没有孩子却有老人,老人叫发爹。不是桂姨的亲爹,是桂姨父亲开茶馆时的伙计,发爹无儿无女,只有一个承嗣的侄子。桂姨爹去世后,茶馆停了业,桂姨把发爹留在家中,一起过日子,桂姨对发爹很孝敬,衣食住行照顾得很周到,象亲爹一样服侍。
一家人日子过得很祥和,很和睦。发爹一天比一天老了,腰弓了,眼也花了。桂姨时常就着她家那盏玻璃罩灯,在那暗淡昏黄的灯光下给发爹剪脚指甲。满身的老人味,满脚的臭气,全然不觉,低着头,柔柔的手,轻轻地,细细地剪着,修着。每天端茶倒水,给发爹洗脸洗脚,一年四季为发爹添衣保暖,缝补浆洗。
发爹病倒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住进了医院,胆结石,要开刀。八十三岁的老人,桂姨不好作主,终究不是自已的亲爹,桂姨请来了发爹的侄子。开刀后,发爹情况不好,弥留之际,桂姨对发爹说:有什么事要交代,还有什么钱,什么东西,要对你侄子说清楚,交给他。
发爹满眼泪珠地瞅着桂姨不吱声,只是摇头,紧紧拉着桂姨的手。
“发爹,你说,你说清楚了好。”桂姨轻声执拗地劝说。
……还有四百六十元钱放在衣箱……。
当晚发爹去世了。他侄媳急叉叉地赶来,打开衣箱,四百六十元,一叠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儿。(1977年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媳妇心安理得地揣进兜里走了。客气话也没撂一句。
母亲为桂姨愤愤不平,这娘儿怎么这样不讲理,干妹子你服侍了发爹这多年,这些钱还不是你给发爹他攒下的。这娘儿生前不来倒口茶,端杯水,送上一菜一汤的,人才死倒会来要钱。干妹子你也太好说话了。我就咽不下这口气,走,我给你出这口气去。
母亲气愤不已,桂姨却心平气和,说:姐,别这样,这样我倒心安,要不我就不催发爹说,我把发爹当亲爹,用些钱,服侍他,我情愿。
母亲见桂姨这么说,也就算了,只是心里为干妹子不服气。
发爹去世后,桂姨很伤心,心里闷,就往母亲这边跑,帮我母亲做做事,和我母亲唠唠话说说家常。两姐妹虽然脾气不一样,却相处得很好,你帮我我帮你,胜过亲姐妹,好象她们之间有一条血缘的纽带缠绵在一起。
其实这胜似血缘的缘带不是别人,而是我。谁叫我母亲把我送给桂姨做了养子呢。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的这句话:桂姨她人好,心好,把你给她,娘舍得,愿意。
作者简介:
刘志平,男,1955年生人。汉族,小学毕业之际,因文革而辍学。1983年参加江苏省高等自学考试,获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凭。一生爱读书,不求甚解,喜舞墨弄文,收效甚微。
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雨花》《散文选刊》《散文百家》《青春》《牡丹》《岁月》《金山》《文艺家》《三角洲》《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500余篇,部分作品获省市级文学奖。
小说《值八文》被《传奇传记文学选刊》选载。小说《对号入座》《故乡人物二题》散文《生活感悟》《消失了的周庄》《青花大碗》入选南通当代作家丛书一二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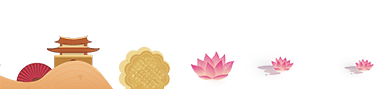
协办单位:《芙蓉国文汇》、《品诗》 主编:陈智鹏 (萧逸帆) 副主编:应永 编辑:安瑞刚 王建雄 胡拮 心森 第七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征稿 投稿邮箱:xingshiyuekan@163.com 投稿作品必须原创首发,拒绝一稿多投,所有原创作品都将受到原创保护。 所有的来稿,我们都会认真审阅,入选作品会择优在《品诗》公众号上发表,并有机会入选《芙蓉国文汇》第九卷一书。没有选中的稿件,我们也会及时回复,不要气馁,欢迎再次投稿。 征稿要求: 题材和体裁不限,一切以作品说话,发掘新人,鼓励创新。请投稿之前仔细核对错字和标点符号,否则一概不予入选。 投稿格式: 邮件标题:第七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姓名+作品名。邮件内附上作品、姓名、电话、通讯地址、邮箱、100字以内的个人简介。 诗歌5首以内,总行150以内,组诗100行以内(旧体诗词5首以内)。 散文2篇以内 微小说3000字以内 可以任投一种体裁或多种 奖项评定: 小说、散文、诗歌奖分设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另设人气奖1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