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我家七十年》连载13
崔兆森 口述 公晓慧 整理
编者的话
崔兆森喜欢看电影,还喜欢“ 读电影”,他收藏了从创刊以来到现在70 年的全套《大众电影》。守着这些历经时光的杂志,崔兆森更像是虔诚地守护着一段过往的岁月,一种历史的情怀。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校里就经常组织我们去看电影。我在学校里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根据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普希金的小说改编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那是一部进口的彩色电影,看到渔夫和金鱼能在一张巨大的幕布上行走、说话,故事的美丽画卷和故事情节,让我们激动得嘴都忘了闭上!
回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老济南的电影院非常多。1953 年,济南一下子盖了三座新的电影院—十二马路的明星电影院、天桥北头的光明电影院和人民商场的中国电影院。三座电影院从外观上看起来, 都是民族形式的“ 大屋顶”,富丽堂皇的。从现在依旧“ 健在”的明星电影院的外观上,就能依稀看到几十年前老电影院的旧日风貌。除此之外,还有大观、职工、军人、和平、新华、中苏友好电影场等十多个电影院。
这些电影院的生意都火爆一时,这种火爆甚至延续到20 世纪90 年代初。只要张贴出新海报,影讯很快就传遍整个济南,电影院里场场爆满。一个电影院,楼上楼下能装下近千人,从早到晚,不停地在放电影。就是这种排片密度,不少人为一张票,凌晨四五点就去排队买票,等几个小时也不计较。说电影票一票难求,真是一点不假。虽然一票难求,但那时候的电影票的确便宜,两毛钱就能看一场。看电影是那时候年轻人谈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大人给介绍对象,就是买两张挨着的电影票让年轻人去看电影,说不定就能促成一段婚姻。
我平生看过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是《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无巧不成书,我看到的第一本《大众电影》的封面,竟也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做封面的那一期!1953 年10 月那一期,《大众电影》的封底图像是从电影中截取的一个精彩画面,里面还有关于电影拍摄花絮的介绍。65 年前,一本杂志的彩色封面和有关电影故事的文章,带给我的惊喜和震撼,无异于一部彩色电影带来的震撼,甚至还能超越电影带来的冲击。因为电影毕竟一看而过、转瞬即逝,杂志却可以长久地存于身边,随时翻看,常看常新。
后来,我从地方到了部队,当文化干事,巧的是,让我分管电影组。我们经常下连队为基层官兵放电影,当然,放得最多就是“ 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再加8 个样板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来自阿尔巴尼亚、苏联和越南的电影,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放电影时,所有官兵都坐在一个大操场上,一半看正面,一半看反面。有一次放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这个镜头正放着,下个镜头的台词观众就一起喊出来了。翻来覆去就这几部电影,大家看了一遍又一遍,台词早都背过了。后来,我常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和收集有关电影的资料,我和电影、和《大众电影》的缘分,又一次续接了起来。
一直以来,《大众电影》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中国电影的变迁史和成长史。当改革开放大幕缓缓拉开之时,沉潜于“ 三大战”十余年的中国银幕又悄然“ 变脸”。1979 年《大众电影》第5 期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和玫瑰花》男女主角拥吻的剧照。这在现在看来十分普通的一个镜头,当年着实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叫问英杰的读者愤然投书质问,“ 你们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
丰富的电影资料, 使我有条件对此次舆论风波保持了持续关注—我看到,《大众电影》编辑部随即在当年第8、9 期上开设“ 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专栏,在当年第10 期上告知读者“ 两个月时间内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 多件,最多时一天收到来信近七百封”, 还在刊发《寒流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读者来信综述》一文中称,“ 从已经收到的读者来信看,赞同他的观点还不到百分之三。”“ 这次把读者提出的问题公之于众,测出了是非,测出了人心的向背。”
这之后,原本就风头无两的《大众电影》,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1981 年,也就是它复刊的第3 年,最高发行量达到了947 万册—这几乎相当于当时7 亿人口中,每70 人就有一本《大众电影》,创造了电影杂志销售量的世界纪录。当时,能买到《大众电影》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好像谁能买到谁就是能人一样。它的发行渠道只有邮局,连新华书店都买不到。
关于《大众电影》的收藏之路,始于1994 年10 月。那时,女儿刚刚离家去北京读大学,老伴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在两个卧室之外, 多出一间12.5 平方米的房子,可以当书房。在布置书房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二十多本旧《大众电影》。静静地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翻阅已然泛黄了的页面,沉睡在脑海深处的中国电影往事,又一帧一帧开始重放。
1953 年10 月,《大众电影》封底:《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就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想多收集一点《 大众电影》。凡事靠一个“ 定”字,靠着持久的定力,此后十余年岁月中,逛文化市场、旧书市场,就成了我重要的业余生活。我跑遍了济南之后, 也到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地,“ 众里寻她千百度”。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上海的多伦路、文庙,以及南京、武汉、天津这几个大城市的文化市场,只要出差到那里,我每次必去。这样便逐渐收集全了。
但也有一些是在文化市场上找不到的,我在2001 年的《大众电影》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谁来圆我的〈大众电影〉收藏梦》的文章,然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藏友的信件,提供线索甚至无偿赠送杂志。
在全国各地藏友的帮助下,到2002 年,就只差创刊号这一期了,遍寻不得。2004 年10 月13 日,潍坊藏友聂传声先生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说济南成通文化城出现了《大众电影》的创刊号。我匆匆赶过去,确认无误后,赶紧回家取钱,最终以2800 元的价格把《大众电影》创刊号带回家,全套终于收全。至此,收藏《大众电影》的愿望算是最终达成。
1979 年第5 期《大众电影》开创用电影演员生活照做封面的先河(封面演员为陈冲)
2002 年9 月30 日,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致电之人自我介绍是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的制片孙庆石。他说,央视《实话实说》要做一档全新栏目《电影传奇》,他们去《大众电影》杂志社想借阅相关杂志,获知杂志社也没有存留全套杂志。但他们也同时获悉,全中国有两个人有全套杂志,一位在东北,另一位就是我。
一番对话如下展开:
“ 崔老师,能不能购买或者租用一下您的全部杂志?”孙庆石问。“ 我的收藏不卖也不出租,可以无偿借给你们用。”我告诉他们。“ 太好了,明后天我们派四个人到您那里去拿一下。”孙庆石一开始有点难以置信,旋即兴奋地表示要派人来取杂志。
“ 不用了,正好我要去北京出差,我给你们捎过去吧。”
放下电话后,我把全部杂志码好,装了满满五个大纸箱子,到了北京后把它们送到了栏目组。用了一年时间,栏目组把所有《大众电影》杂志逐本扫描,制成电子文件。2004 年4 月3 日起,CCTV一套《东方时空· 周六特别奉献》中开播了一档别开生面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每期讲述一部中国电影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中轶闻趣事。在栏目组制作的广告册中,在“ 特别鸣谢”4 家电影机构—上影、长影、八一、中影集团之后,还出现了以下字样——《电影传奇》广告
“ 我们还要感谢山东的崔兆森先生和支持我们的所有朋友,他们将珍藏的电影资料提供给我们,让我们对过去知道了很多。”
2001 年第1 期《大众电影》刊登我写的《谁来圆我的〈大众电影〉收藏梦》
《大众电影》刊登陈志超的文章《寻寻觅觅十年路 一步之遥大团圆》介绍我的收藏故事
后来,有一次,当时的《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见到我,感激地说了句:“ 山东人真仗义。”我才得知,他们在找到我之前,先联系了另外一位收藏家,但他根本不外借杂志甚至连看都不让看一眼。
2016 年 9 月,我的这套跨越66 载近千册《 大众电影》被评为当年“ 山东民间收藏十大精品”之首,我也荣膺“ 山东民间十大收藏家”称号。在后来创建家庭博物馆时,截至2019 年4 月底,我把上迄1950 年创刊跨时70 个年头958 期《大众电影》杂志放进了博物馆,并把所有封面制作在三个展板上。有趣的是,每次来人参观,都不自觉地走向自己熟悉的展板。像我这个年纪的,肯定是对第一块展板里的电影明星最熟悉,比我们年轻一些的对第二块展板的明星比较熟悉。一天,来了一群“90 后”的孩子,他们其中一位指向一张封面,跟我说:“ 这是鹿晗!”他说的这位新时代的电影明星,我们这个年纪已不知道他是谁了。
1966 年第6 期总第306 期停刊号毛主席和阿尔巴尼亚谢胡
2019 年第3 期总第957 期至今我收藏的最后一期 《 大众电影》电影演员潘粤明
(《家庭博物馆里的中国——我家七十年》 崔兆森口述 公晓慧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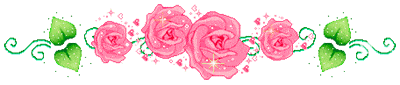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