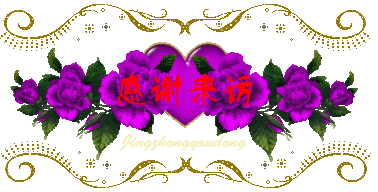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中学教师,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厦门市作家协会会员。集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生活 创造》《福建教育》《厦门教育》《集美风》,厦门日报晚报等。爱旅游,爱阅读,爱写字,渴望凭着文字,与你,与世界自如地交流。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优雅》、《一杯茶的幸福》、《最美的时光在路上》,厦门女作家合集《遇见》。



记忆里那些割稻的日子
福建·柯月霞文
烈日炎炎,撑着伞走一小段路,便满脸是汗,不禁想起年少时那些在烈日下割稻的日子。
那些年,仿佛暑假的铃声一拉响,稻田里的稻谷便跟着熟了,我一回家放下书包,便转身拿起廉刀,跟着父亲母亲,到田地里去割稻、打谷、耕地、插秧,成了彻彻底底的一个农人。
那些年,农村生产已承包到户,我们家的田地虽然不很多,但同样得收割好几天。我们家总是自己割稻,不像有的人家,是两三家聚在一起割,割完这家割那家,这样合作割稻有个好处,就是人手多,好安排。女人割稻,男人打谷,小孩们帮忙从地上抱起稻谷,递给踩着打谷机的男人们。
我们家自己割稻,人手不够,便要巧妙安排。总是这样,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先一起割稻,割了一半后,留下母亲一个人割,父亲和我两个人便去打谷,父亲一个人踩着打谷机,我抱稻谷给他。
有时妹妹也来,而母亲也割完稻谷了,便是我与父亲一人一边踩打谷机,母亲和妹妹抱稻谷,虽然这样自己割稻比较辛苦,但是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往往不用几天,便能把自家稻收割完毕,不像几家合作割稻,拖拖拉拉,总要忙够十天半个月。

割稻的那些天,我们一家都要起得特别早,吃罢早餐,便拿起母亲早就准备好的键刀、扁担、麻袋等等工具,戴上斗签,然后母亲推着独轮车,我和父亲一人一边抬着打谷机,一起向田间走去。
到了田里,母亲总是抢先站到最边上,挥起镶刀,弯下腰就开始割起稻来,我挨着母亲数了六行稻站好,然后弯下腰,左手抓住一把,右手用键刀一挥,往稻草的根部一割,再顺势往下一把稻草根部割去,每割一下,便发出“哪”的一声,于是,随着一阵阵“哪嚓响”的声音,稻子缓缓往我左手边的田地里倒去,渐新地田地里便躺倒一大片稻子,就如操练的士兵一样排得整整齐齐。割稻看起来是体力活儿,但其实还是要靠巧劲,所以尽管我咬紧牙根埋头苦干,但因为经验不足,还是很快便被母亲远远甩下一大载,母亲割完一越,又从背后赶上我时,我便只能把自己的这一越给母亲,转身向后边去割,很多时候我为了不让母亲超过自己,便头也不拍,两手不停地割着,长时间弯腰酸得实在受不了时,我便暗暗为自己鼓劲,比如坚持到这一越割完才抬头停手,下学期期末就能考进班级前五名等等这样的心愿来鼓励自己,就像牧人抓着一把青草引诱着一头牛往前一直走,就这样自我鼓励着把一行行稻子割倒在田间。

和父亲一起踩打谷机对我而言是一种挑战,毕竟这是一种属于男人的体力活儿,很少看到女人踩打谷机的。所以虽然辛苦,但我反而有一种自豪感。我一脚站立,一脚配合着父亲的节奏踩着打谷机,双手捧起一大把稻谷,往打谷机里送,等到一边的谷粒甩完了,再翻转另一边继续甩,这动作看起来容易,其实很不简单,要手脚配合得好,又要眼神好,该甩该翻,该伸进去,还是拿出来一点,都要仔细观察,并立刻做出判断。所以我总是没干多久,就累得满头大汗。
其实,割稻、打谷,还不是最艰难的,我最怕的是回来的路上。
我和父亲一人一边抬着打谷机,总是觉得举步维艰。那打谷机在水田里浸了大半天,显得愈发沉重,我觉得自己的肩膀实在快被压碎了,背就快被压弯了,再加上头顶上的似火骄阳,脚底下的如热碳的沙路,真像是在熔炉里炙烤一般。
不过,割稻也有充满诗意与乐趣的时候。那是碰巧遇到月半,月色很好,父亲便会安排我们晚上去割稻。吃过晚饭,我们来到田里。彼时,晚风习习,流水涂凉,田野里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几声夏虫的呢哺,像是一阙优美的小夜曲。依稀月色中,我们手握镶刀,一把一把,一行一行,把稻谷轻轻地割下,轻轻地放倒在田地上,割累了抬起头,擦擦汗,望望天边的月亮,或是坐到田填上,聊聊天,空气里散发着稻谷的芳香,混着青草味儿,深深吸一口气,感觉满怀满心都是清新纯净的。
于是那些割稻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变得亲切美好起来。



退役的菜橱
每当我把还飘着诱人香味的各色菜肴,倒进垃圾桶时,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的那个菜橱。
童年里的一日三餐再简单不过的了,早餐、晚餐是稀饭,配稀饭的常常是萝卜干、齐菜梗,如果炒萝卜干时能放上一个蛋,煮芥菜梗时能放几条小鱼,那对我们来说无疑就是美味佳肴了。很多时候,妈妈只是从岔里掏出几条萝卜干或者芥菜梗,洗净,往盆里一放,就算我们两、三天配稀饭的菜了。
只有中午才有机会吃到干饭。配干饭的菜,也是极其简单的,往往都是自家种的丝瓜、葫芦,或者高丽菜、空心菜,反正地里种什么就吃什么。记得夏天常常是丝瓜煮汤,素炒空心菜,冬天就一直炒高丽菜,煮萝卜汤。有时一连十天半个月都吃同一样菜,我们也一样吃的津津有味,毕竟能吃干饭,就有炒菜,有炒菜就有一点油腥,这对于成长中的时饥饿着的肠胃,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慰籍了。
看起来似乎没必要菜橱了,吃都吃不够了,哪还有剩菜放进月菜橱呢!可就是那么巧,我们家有棵树被台风刮倒了,又凑巧有个参军回来的邻居,刚学会了木工,想练练身手。于是父亲和那小伙子就一拍即合,请他用那棵树做一个菜橱,工钱是10元人民币。那小师傅带着工具在我家,又是创,又是锯,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星期,终于大功告成,一个漂亮的菜橱呈现在我们面前。
主体部分的两扇门还加了尼龙纱,以防蝇虫、蜂蚓,这门还能上锁,以防老鼠和猫狗闯入。菜橱最上面的一格,可以放锅、缸等大件东西,下面是两个抽屉,最下面的一格摆放碗筷。

那两个抽屉,我和妹妹一人分一个,我是右边的那一个。记得有一次,外婆给我了几个红艳艳的荔枝,我剥开吃了一个,那鲜美的甜味简直让我太惊喜了,我再也舍不得吃第二个,于是小心翼翼收藏在抽屉里,想留给下地干活的妈妈吃。可是我后来居然把这事忘了,直到好几天后不经意拉开抽屉一看,那几个原本鲜艳欲滴的荔枝,早已变成干枯暗淡,皮也烂了,一碰便流出浓浓的酸臭味来。那一刻我非常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懊悔!
身为家中老大,我很早就能独挡一面了,放学一回到家,就开始提水,做饭,喂猪,农忙时父母在田里加班时,我还把饭菜提到田里去,然后回家把剩下的饭菜分成三份,打发两个妹妹就餐。记得那时配稀饭的菜都做得很咸,一餐饭常常配不了几个菜,大概是没时间经常做菜吧,妈妈每次都做很多,所以,没吃完的菜就放进菜橱里,下一餐拿出来继续吃。
菜橱里还放着做菜用的油。那时偶尔父亲会买回猪油,下锅炸好了,盛在一个小盆里,放进菜橱里第二天就变成白白的固体了,用汤勺挖一小勺,就够炒一个菜了。父亲用油很节省,所以每炸一次油,就可以撑好长一段时间。
有次,父亲一时兴起,非常慷慨地挖一勺猪油,给我们姐妹碗中的包菜咸饭各加了一点,那白花花的猪油在热饭里慢慢融化,诱人的肉香阵阵飘起,那餐饭,吃得我甜畅淋漓、那滋味至今难忘。此后的几天,我都偷偷地打开菜橱,偷偷地用汤勺挖一点猪油,埋进咸饭里,然后裹着自责与罪恶,大口大口地嚼着。直到有一天,父亲端详着那盆猪油,疑惑地自言自语:这次猪油怎么用得这么快?那天之后,我再也不敢偷吃猪油了。
后来,农村经济好转了,我们家也有了冰箱。这个菜橱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我们家的厨房重地,被妈妈放在另一个屋的角落里,连同那些淘汰掉的锅碗瓢盆一起,默默相守着,守着那一段忍饥挨饿的岁月。






主编微信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