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清明不仅是祭扫的仪式,更是生命的课堂。又是一年的清明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对逝者的追思与缅怀。
怀念何茂业(中)教授
清明酒,让记忆流动;清明议事,让智慧传承。 青年人的使命,不是仅仅重复仪式,而是让古老的清明,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意义。
三成为「未来的播种者」:清明正值春耕,可效仿古人“墓田植树”的智慧,将祭扫与环保结合。 思考自己希望被后代记住的方式——这决定了你今天如何活着。
最好的传承,不是重复过去,而是让传统与未来相互照亮。 也许既不必全盘照搬三跪九叩,也别让清明沦为打卡式的假期。当人们用属于世代的方式诠释“慎终追远”,那些长眠地下的眼睛,或许正透过新绿的柳枝,向我们微笑。
感谢关注语墨东江文化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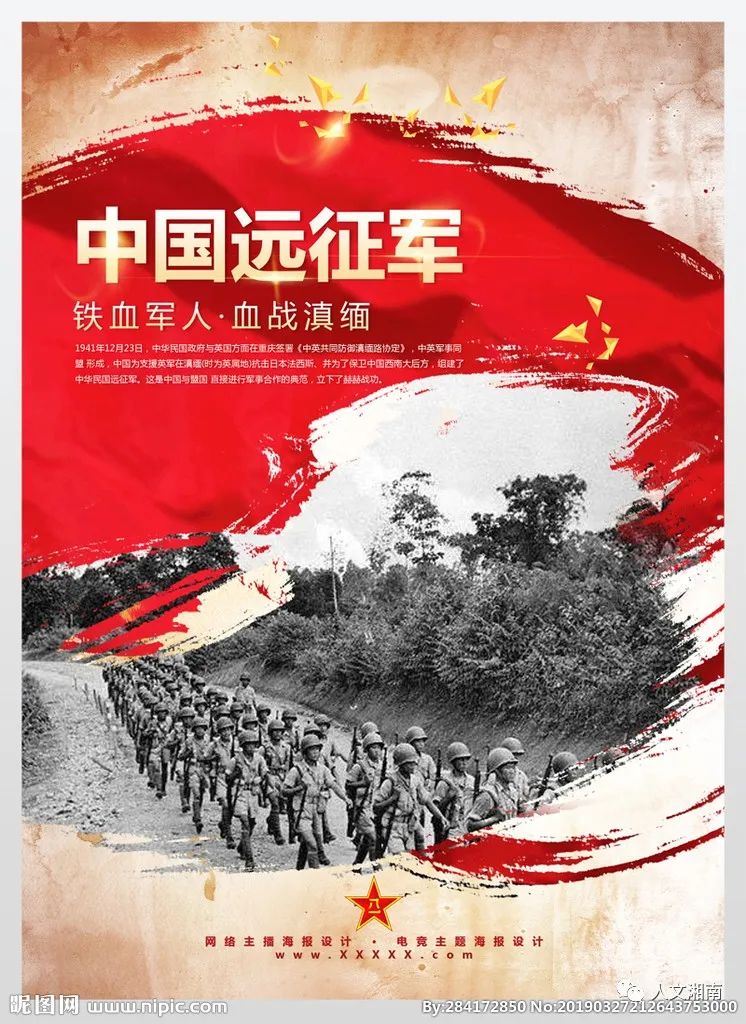
在抗战史上,有一个特殊群体——中国远征军,远征军中有一个团的大部分官兵均来自郴州,其中张湘少校就是郴州人。
负笈求学,成家立业
张湘,本名叫张达杰。他是家中老大,老二叫张达伟。张湘是他入伍后,因身在他乡,思念故土而给自己起的别名。自此,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军队,交给了那个年代的战争。
1911年6月10日,张湘出生于郴州资兴一个边远偏僻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叫龙合,约有五百年历史。龙合村子虽小,却有个叫“书房脚”的私塾,祖上曾出了个秀才,名叫张翼舒,又名守富(守字辈),这便是张湘祖父的祖父。张湘的父亲名张岚生,是张翼舒的长子,娶渡头花园村的刘氏为妻,刘氏嫁到龙合后改名为白花(张翼舒的儿媳,按当地习俗,女子嫁进来后都要起一个带“花”字的名)。
张岚生家中虽然贫穷,但却送其大儿张湘读了许多书,从私塾到高小,从衡阳初中到湖南第一师范,以至后来有机会参军,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加入中国远征军。
为了送儿读书,张家一贫如洗,张岚生累死累活一辈子,死后三年也未能下葬,直到张湘忙完军中大事,才回家奔丧,安葬老父入土为安。
张湘1926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留校任教一年。1927年末,张湘回老家,看到家乡急需人才,于是决定留下来在家乡当一名教书先生,把所学知识传授给孩子们,为家乡培养人才。他任教的小学就是当年渡头江畔的泸溪学堂。
两年后,张湘由一个毛头小伙长成为英俊青年,19岁的年华,书生意气,风华正茂。经人介绍,认识了清江玭珠古村一个高挑清秀的女子,其名为李平清。两人结婚后,193O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取名张小凤。一只小凤凰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接下来的日子,他一边教书,一边持家,日子也似乎过得太平无事。1933年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长子张天仕;1937年生下第二个儿子张天明。
就从这一年开始,中日战事爆发,小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了,张湘用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投笔从戎,远征印缅
全中国抗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张湘再也无心教学,投笔从戎的念头在他的脑中不断闪现。终于有一天,一群热血青年在时代的召唤下,相约报名参军。据说,渡头儿女中,一起去当兵的包括丁波(本名李业勤,渡江瓦日塘人,渡头老中医李肖如的儿子)、李业胜、张湘等一行十多人。1937年4月,张湘告别了妻子李平清和还在襁褓中的幼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挚爱着的家乡,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奔赴抗日前线。张湘与丁波相互支持与鼓舞,一路转辗,经衡阳,准备上战场,报效祖国,并约定“他年成事,勿相忘”。
“七七事变”的战火很快烧到了南京,日本飞机在南京上空狂轰滥炸,那一年8月,张湘随部队也来到了南京,他心急如焚,竟然一时晕倒在地上,事后竟无法下床,被湖南籍国军同乡抬着担架,上了汽车撤出南京。
因为这次生病,张湘躲过了一次灾难,却也因此而与丁波分手,错失了与丁波一同去延安的机会。
张湘身体恢复后进入了最强大的国民党税警部队。据称,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总团部直辖特务营、高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营。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淞沪会战爆发,血气方刚的税警总团在一月之间,便集结、编成由一、二两个支队组成的野战部队。
张湘便是这支部队的一员。从1938年10月1日参战起,至12月5日止,税警总团参加蕴藻浜与苏州河阵地守备作战。最后,税警总团主力在周家桥,担负掩护主力撤退的断后阻击。以少抵多,以弱抗强,这支青年学生较多的部队,在周家桥击退日军七次强渡,虽然损耗重大,最后,仍然全身而退。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缉私总队,伤愈归来的孙立人担任少将总队长,进驻湖南一带整训待战。随后,因为之前战损极大,该部不属于野战部队,无法在湖南前线得到及时补充。经宋子文亲自奔波、协调,终于,缉私总队驻防大后方贵州都匀,得到就近补充,继续整训的机会。1939年初,缉私总队元气稍微恢复,重新采用税警总团的名称,仍由孙立人任总团长。1941年12月,税警总团正式改编为国军新编第38师。就此,税警总团,这支最初为宋子文等财经界精英组建,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为控制盐税而建立的武装警察性质的部队,编入陆军第66军战斗序列。1942年初,中国陆军新编第38师成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开赴滇缅前线。
张湘是在中国陆军新编第38师服役,职位是汽车连连长,负责运输军需物质。
这里有个小插曲,龙合老家有一个叫张旺才的人,有一次与张湘在一个小站偶遇,旺才看到了张湘,但张湘没发现他,由于张湘穿的是军官服装,且改了名,不久又各奔东西,终未及相认。
次年,滇缅战事恶化,国军新编第38师退入印度。
在兰姆枷,在美军全力装备、后勤支援下,该部官兵分别接受了美式军事作战体系化培训。张湘也在这个干训班中接受训练。
也就在这一时期,驻印的新38师、新22师奉命整编为新一军。
1943年10月,新一军拉开了中国军队大反攻的序幕。
由于张湘带的是汽车兵,自中印公路打通那一刻起,这条路一直是一条生命之路、血肉之路,张湘用智慧多次躲过敌机的轰炸。有一次敌机追着他的车队投弹,他加足马力往前冲,看到敌机到了头顶马上刹车,敌人的炮弹落在车前方十几处爆炸了,而车子完好无损。有的路多弯且陡,张湘下车用眼睛瞄一下,就能测出坡度,找到行车路径,然后身先士卒,第一个开上去,再下车指挥车队一一过关。张湘的三角涵数很好,三角涵数是炮兵作战时最常用的知识,炮击的角度,张湘张口就来,这无疑在战场应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中亲人不知张湘的消息,以为已战死在沙场。李平清在家拉扯着三个孩子,早盼晚盼,就是不见张湘的影子,以为他永远也回不来了。后来,一位叫才古的好心人与李平清搭伙过日子。吃食堂那些年头,家中靠红薯等粗粮给孩子们充飢,家里连一盒火柴也没有,要到一个叫路清的阿婆家用“皮管”(葵花子茎杆浸水后晒干而成)点火,有一餐没一餐地度日。
张湘往来于云南与印缅之间,根本顾及不到家中大小之事。在云南,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李瑞清,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李瑞清死后葬龙合完烧奇(地名)。
李瑞清与张湘一共生了四个孩子。1943年生下二女儿,起名远征,以纪念远征军出行。1944年生三女儿冰天。1945年生四女儿凯旋,以纪念远征军凯旋而归。之后,张湘离开了云南,把李瑞清与冰天、凯旋送到了郴州,把远征留在了云南,交给他的姨姐夫抚养,而他自己则随部队转战南北各地,连家门也未踏入一步。
去郴州接李瑞清他们一行三人的是张湘的亲弟弟达伟与堂弟六才两人,他们从小溪张家(地名)走小路接回来龙合,在龙合李瑞清还生下了一名男孩,据说因口中生了恶性肿瘤,一岁多就死了。李瑞清体弱多病,时常吃药,在清江积坪还住过一段时间,病重后回了龙合,村子中人去探望李瑞清,据说,李瑞清还给每人赠送了一块“高梁”牌洗脸巾。也有说,张湘回来安葬李瑞清时,还给家族中每人一块银元,唯独没给两个儿子,说是自家人。
战后峥嵘,魂归故里
抗战胜利后,1945-1946年期间,张湘随部分国民党官兵回国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并举行了庄严的授降仪式。1947年,他被授予少校军衔。
1945-1948年,东北内战,国民党军队解甲投诚,张湘也在其中,因他在战争年代救过丁波一命,共产党优待俘虏,得以宽大处理。
1948年,张湘的第二任云南妻子在龙合病故。1949年,他与东北女子关玉燕结婚,生下四个儿女:老大放天,老二冻天,老三人天,老四慢天。
抗美援朝开始前后,张湘曾一度心灰意冷,家仇国恨,积郁心中。年过半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令他疲惫不堪,再没有当年的雄姿英发。
抗美援朝势在必行,此时的张湘想必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既不能为国效力,何不举全家之财力为国效忠?据称,张湘捐了3斤黄金支援抗美援朝。
家中没有了资金,张湘再次以真本事考入了长春汽车制造厂,还不断技术革新,在厂外兼职。工厂为了鼓劢张湘的功绩,50年代,发过50元的奖金给他,以后还固定每月发5元额外工资。
……
张湘于1971回湖南老家安葬母亲。据说,他母亲去世前穿着花绸子寿衣,晚辈摸着老人的大手,那大手还很热乎,所有孙子辈到场后,她才便含笑九泉。
这时的张湘也已经六十有余。退休在外,思念故土,回不去的老家,过不了的心坎。有一次终于当着长春的长子说出了心中的不平:这一生啊,生不逢时,时运不济呀!一声长叹,背过身去,老泪纵横,唏嘘不已。
人生终于在1978年10月4日那天终结,张湘享年68岁。
张湘病故后,龙合的张天明到长春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把骨灰盒带了回来。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只是草草地安葬了一下,致使亲友多不理解。后来,他长春的儿女寄钱过来,其孙子亲自设计,为张湘制作了一幅墓志铭的对联“投笔从戎建功业,走南闯北留芳名”,中间石碑阳刻“张湘(少校)之墓”,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2016年,在众多好心人和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张湘的衣冠冢在云南芒市落成,从龙合张湘的墓上取了些土,还有家乡三年以上的老茶叶,一并邮给了冻天,永久地埋在了云南——张湘生活和战斗过的土地。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马英九先生还曾为张湘这一批抗战老兵签名,颁发了嘉奖令。
(图片来源:网络)





